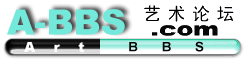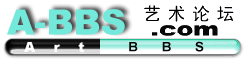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02-05-22 21:55:00
□ 阅读次数:2053
□ 现有评论:0
□ 查看/发表评论 |
|
|
关于传神的中西审美之比较
网络
|
关于传神的中西审美之比较
传神,这是我们民族艺术美学的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一概念的提出,约在魏晋时期,与当时的玄学兴盛是有密切关系的。其祖宗,得追到庄子的“得意忘言”说了。《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里的筌,是补鱼的器具,它的存在是为了补鱼;蹄,是捉兔的器具,它的存在是为了捉兔;而言的存在是为了表达意,只要意到,就不必在乎言之如何了。在庄子看来,言、意是有明显的层次之别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後来的周易就进一步具体化,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王弼以老庄解易,使得意忘言说又有发展。“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得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周易略例·明象》也就是说,与得兔和得鱼同样道理,只要象能“到”,就不必在乎言之如何;只要意能到,亦不必在乎象之如何了。王弼进一步发挥∶“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里,显然把话说到了极端∶仅仅存言,是得不到象的;仅仅存象,是得不到意的。必须忘象才能得意,忘言才能得象。话是“玄”了点,但道理还是明了的。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影响非常广泛。生活中就有九方臬相马的故事,只管马的神气,而连“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列子·说符篇》)。这就是“写意”的始祖。
也许,对传神这个概念的产生更为直接影响的,还是後来《淮南子》。该书虽然是在讲道,以人为本去谈天说地,讨论宇宙、社会和人,但一些论述的本身就与艺术实践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去不远了。“夫性命者与形俱出其宗”(《原道训》,同),首先就把这种关系点了出来。对於“得道者”,“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继儿具体论述,“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地;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二者伤矣。”除了形与生、气与生、神与生的各对矛盾两方面相对关系外,还有三者各自合乎规律的重要性∶“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进一步论述气与神的作用∶“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瞢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在论述因“形神相失”的各种害处之後,又做到结论∶“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明确地突出了在形与神的关系中神的重要意义。当然,这时的形、神与後来在绘画上的形、神不完全是一回事,如许慎在注中就有所为谓“神清静则利,形有情欲故害也”的诠释,但是,当它们在艺术领域内广为所用的时候,後人也就数典忘祖了。
《二》
最早在绘画界明确地使用“传神”这个概念并系统地加以论述的,是东晋的顾恺之。他在《论画》中就提出“以形写神” 的著名论点,对画人物来说,眼睛的传神作用尤为关键。《晋史·列传》卷六十二就曾记载顾恺之有关传神的一段著名语录∶“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於妙处,传神写照,正阿堵之中,”“以形写神”是指在描绘对象逼真的前题下,表现对象精神面貌,气质和风姿,所以他很重视形的准确。他在“论画”中还谈到“若长短、岁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便会导致“神气与之俱变矣。”为了对象形体准确,达到传神的目的,顾还总结了一个方法,即注意与画外人物感情交流的表现。他认为不能“手揖眼视,面前无所对”。假使“空其所对”,则“传神之趣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因为“一象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明也。”显然,这些理论与《淮南子》中关於形、神的探讨是一脉相承的。
一百年後,南齐的谢赫又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是中国艺术美学上的第一次系统总结,被後人誉为“千载不易”的理法,其中第一法就是“气韵生动”。这里的气韵,还是指人的精神面貌,气质和风姿,这实质上还是顾恺之的那个传神论的发展和具体化。相对来说,他突出了“气”字,与顾氏突出“神”字略有差别。也许,明显的“区别”还在言论上。谢赫竟批评顾恺之的作品∶“迹不逮意,声过其实。”也就是说,顾在言论上叫的响,但在实际创作中并不到家,未能表达自己的立意,而谢赫的气韵说,则特别强调传神,在他看来,一件作品只要能做到传神,那怕形似略为不足也应是上乘之作,而形似很好但传神略逊一筹的也只能甘居末流。
不过,後人似乎并不以为然。如又约莫过了一百年,陈的姚最在他的“续画品录”中评论谢赫说∶“笔路纤弱,不似壮雅之怀”,并认为他在“点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但是,“至於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这意思,几乎可以用谢赫批评顾恺之的话来还给谢本人了。在过了二百年之後,唐张怀 评价顾时说∶“象人之美,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这是他在《画断》中提出的见解,并且是把顾恺之与张僧繇、陆探微对比而论。他还进一步赞扬顾∶“运思精微彻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传神达到这般境地,真可谓“神”矣!如此看来,顾、谢两位首擎“传神”大旗的开山人物,似乎在传神与写形问题上出现了一些矛盾的现象。也就是说,顾在理论上是强调“形”的,但在实际上更重视“神”;谢在理论上是强调“神”的,但在实践上却更重视“形”。
这一纵向比较,似乎比出了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恰恰反应出了时代的前进、艺术的发展。在理论上,谢比顾更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绘画创作中的一些基本技法经验,对於传神的内容,也作了具体的充实。《淮南子》中有“形”,“气”,“神”三者,顾突出了“神”,谢突出了“气”。“气”者,生之充也,更强调一种原动力。他还融合了魏晋以来在文论界的诸如“神气”、“风骨”、“风力”等内涵;《世说新语》在《赏誉》、《任诞》等篇中对人物的品评,就很侧重所谓“风神高逸”,“风气韵度”等等。“气”、“风”都有一种动感,与顾恺之的“神”的静感略有变化。在技法上,顾恺之所在的年代,承继汉代遗风,绘画主要靠线,造型简约。色彩多为平涂,单纯淡薄。在这种情况下,顾提出“以形写神”;强调形似以保证神是很正长的事。不过,囿於当时的材料和手段,再强调也还是一种简略的勾勒,依旧带有一股原始稚掘的自然味。顾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不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而一百年後的谢赫的年代,佛教艺术影响渐深,材料、手段渐渐丰富,谢自己就总结了六法,所要照顾的面更广。而气韵说的提出,相对於传神说的概括,它更具体、更复杂。也就是说,这时已明确提出了造型准确、色彩丰富和构图完美等要求了。再强调传神,这个时代绘画难免後人看了觉得“笔路纤弱”,“点刷研精”,再往後,中国绘画技法臻于成熟,由重彩色而变为重墨色,由尚繁而转为尚简。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有一段著名的评论∶“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作为一个画家,“不患不了,而患于了。即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其不了也。”《论画体》居於这种时代的审美追求,人们重新欣赏顾恺之的原始稚拙的自然天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
也许更能体现历史发展的,还是传神这一概念的内涵的变迁。顾恺之的“传神阿堵”也好,谢赫的“气韵生动”也好,均侧重在“传”出被画对象的“神”。“形、气、神”都是为对象的“生”服务的。直至张彦远,也还是认为只有画人才有传神的问题,“至於台阁树石,车与器物,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人以外的描绘对象,是没有传神一说的。
到了宋代,文人画兴起,传神的涵义逐渐由传对象的神到传主体的神演变。其代表人物当首推苏轼。他的《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几乎成了文人画的纲领。还有,“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跋汉杰画出》)南宋陈去非的诗句“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臬,“乾脆把古老的典故又抬了出来。而邓椿在《画继》中,则明确地纠正了张彦远之前的“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的观点,也就是说,物和人一样,都是有神的。这里的神,已经有很多作者自己的成分了。郭若虚在《图画见闻》中就有过论述。他认为画应“得自天机、出自灵府”,“发之於情思,契之於绡绪”,而且认为“自古其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颐钩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画”(论气韵非师)。
对此,苏轼论述得更为具体,他的“天工与清新”的境界的实现是有前题的,那就是“神与万物交”,只有这样,才能“天机之所合,不强而能记”(《书李伯时山庄图後》)。又如,谈到文与可画竹能“无穷出清新”,关键就是“其身与竹化”(《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鹤林玉露》罗大经《论画》中还有一段类似的记载∶“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迈逾精,余尝问其有传乎?无疑笑曰∶‘事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尽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这里,也可谓其“身与虫化”了,当然,更为生动的还是苏东坡自己酒後画竹壁上的题诗∶“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芽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也就是说,这里画的是竹,是虫,而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了。
元代的倪瓒,又将此推前一步,他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甚者,“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否,叶之烦与疏,技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清门阁遗稿》)到清代的石涛,更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见之於他的(《画语录》)及一些题画诗跋。“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於于予也,予予脱胎於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旧於大涤也。”(《画语录·山川章》)并且明确宣称∶“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画语录·变化章》)而他的“不似之似似之(《画题跋》)的名句还一直沿用至今。而显而易见,上述的传神侧重已经不是对象而完全是主体了。用西人的说法,则是在表现自我了。
以上就是中华民族艺术传神的渊源和变化,这是一种纵向的比较。站在传神的角度看画家(顾恺之和谢赫),看出了时代的前进,站在画家(顾恺之和苏轼)的角度看传神,看出了境界的发展,随著时代的前进,将来还会有更新的发展。
|
|
现有评论:0 [查看/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