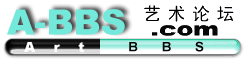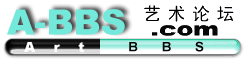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10-02-04 09:55:04
□ 阅读次数:2398
□ 现有评论:0
□ 查看/发表评论 |
|
|
因拆迁改变的利益链
中国新闻周刊/万佳欢
|
2009年12月29日,艺术家肖鲁在正阳艺术区的废墟上生起九堆火,因为站在废墟上让她感觉“特别寒冷”。
这是一个为了“暖冬计划”而即兴创作的行为艺术作品,旨在“针对入冬以来北京朝阳各大艺术区面临的突发性腾退拆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瞬间,肖鲁似乎又回到了80年代。用她的话说,参加“暖冬计划”的艺术家作品都有一种自发的激情,作品“很粗很自然,充满了火药味和革命的声音”。
在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肖鲁朝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著名的两枪,并直接导致这个被称为“中国前卫艺术分水岭”的展览闭幕,之后她跟许多艺术家一样,远走他国。时隔20年,肖鲁在北京东营艺术区的工作室也面临被关的命运,因“市政规划和土地储备的需要”。
艺术创新在意识形态下戛然而止
1979年,在跟西方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尚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的肖鲁已经从上海的“12人画展”、北京的“新春油画风景和景物展览”,以及年底的“无名画会展览”和“星星美展”中,看到很多人在偷偷尝试这与革命现实主义无关、却与西方现代艺术早期样式有关的艺术。
而这些革命性的艺术实验展览都是顶着层层压力、完全在民间组织进行的——“星星美展”的第一次展览刚一开始就被警察赶散。
在国内的报刊上,肖鲁很少能看到现代艺术作品。就在1983年,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栗宪庭由于刊登了一整期的抽象主义作品,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整肃中被撤职。
1985年开始,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艺术终于在中国衍为激流。在这场轰轰烈烈的“85新潮美术”运动中,人们开始自发地形成文化批评思潮。
1987年3月,艺术批评家高名潞在北京组织了第一次筹展会议,却由于随后全国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夭折。此后,《美术》杂志与当时国内众多美术刊物上,对当代艺术的报道几近绝迹。
“那时候(环境)确实很严峻,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回潮,官方对当代艺术、前卫艺术参取一种压制的态度,” 高名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直到1988年,政治环境才相对松了一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现代艺术展览”终于在1989年2月5日开幕。展览开幕2小时后,26岁的肖鲁为了完成自己的行为艺术《对话》,当场朝自己的装置作品开了两枪。美术馆立即陷入一片骚乱,大批警察赶至现场,男艺术家唐宋被作为枪击者拘捕,肖鲁则在下午五点向警方自首。展览在下午3时关闭,美术馆方面以春节为由宣布闭馆五天。
中国现代艺术的萌芽似乎随着那一枪戛然而止。策展人高名潞被迫停职;三天后肖鲁被释放,随即与唐宋一起远走澳大利亚。90年代以后,当代艺术在政治环境变化、社会经济改革冲击和主流社会的压制下日益式微。
“又搬错了”
艺术家们“流浪”的时代其实始于80年代中期。当时有一些艺术家开始脱离体制,聚居在圆明园,靠卖画给一些外国人为生。
那时,他们被政府称为“盲流”。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拆除后,他们不得不搬至六环以外的宋庄。
某种程度上,如今的肖鲁正在体会那些艺术家的境遇。2009年8月,她前后三次在自己位于东营艺术区的家门上收到拆迁条,内容大概是乡里所有的地都是建“大望京”的储备用地,政府要全部收回、拍卖给开发商;东营一带即将拆迁,要求住户11月之前必须离开。
1997年,肖鲁刚回国时,中国的艺术市场经过多年的开放,正日益健全。 “这时的艺术处于一种转折时期,国内一些艺术家的创作也比较多样,” 高名潞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即便当代艺术在往好的方向前进,但那时的艺术聚居区并不多,艺术家们大多在家中进行创作。定居北京后,肖鲁先是跟别人在798艺术区合住,后来又在呼家楼找了个公寓。
找房子成了大问题。首先是这样的房子不多——北京原来的艺术家聚居区也就只有798和宋庄;其次是价格,“那么大的房子,一年得有二三十万才能供得起,”肖鲁说。
90年代末以后,一些国家机构和美术馆也开始做艺术展,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被艺术批评家费大为称为“官方开始认可当代艺术、体制主动向当代艺术示好的标志”。高名潞说。
2006年起,当代艺术在市场上的走势渐好,作品纷纷卖上高价。开发商一看艺术家有钱了,一下子在北京弄出来20多个艺术区。
在那一年的嘉德拍卖会上,肖鲁著名的旧作《对话》以231万元卖出。她在东营艺术区租下了一个300多平米的房子,房租是每天每平米0.75——每平米比798的最高租金便宜了整整5块钱。
当时的东营已经有不少人居住,物业的说法是他们跟村里签了20年,肖鲁便放心地精心设计,花了30多万进行装修。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两年。
12月7日,肖鲁终于收拾好行李,仓促搬到蟹岛西艺术区。令她哭笑不得的是,自己搬过去没多久,那里也被贴条了。“又搬错了,”她摇摇头说。
现在,找房子又一次排上了肖鲁的日程。她挨个前往上苑艺术村、环铁艺术区,甚至天津和北京交界的一处地段看房。“只是现在已经没兴致装修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参加这次维权的“暖冬计划”前,创作风格和习惯都极其个人化的肖鲁从未参加过任何集体性艺术活动,她把自己评价为“一个与这种社会活动有距离的艺术家”。
一开始参加“暖冬计划”的策划时,肖鲁描述自己“完全是因为听到正阳艺术区被开发商停水停电感到气愤”。但她逐渐发现,通过这个活动,自己跟“社会”的距离正在拉近。
肖鲁还渐渐发现,现今的环境也许比创作环境严峻的80年代更为复杂——因为除去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现在还夹杂进来一些商业性、利益性的东西,“如果看不到盈利,或者说跟更大的商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艺术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跨界研究所所长吴学夫曾在一次网络访谈中指出。
而另一方面,资本或市场的进入也许还给当代艺术带来了其他的负面影响。“它好像给了艺术家自由,但是实际上又不自由。艺术家缺少独创性的冲动,容易模仿、重复、追逐市场上的那种时尚,艺术也就容易走向一种媚俗。”高名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对于今天艺术家被驱散,在他看来也未必完全糟,“边缘化艺术家反倒可能会是新艺术的希望”。★
因拆迁改变的利益链
当艺术成为契机,让一群原本不相干的人共同描绘一幅亮丽图景时,他们忘却了脚下是流动的沙地
本刊记者/王婧 文/周潇枭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艺术家李象群试图像五年前挽救798艺术区那样,再次挽救朝阳区东北角的一大片艺术区。当年,他从建筑、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奥运五个方面分析了798存在的价值,最终798成为北京政府首批授牌的“文化艺术创意产业园区”之一。
但这一次,李象群忧心忡忡,他觉得这片艺术区已不可能保留,“必然会拆迁,因为这是北京市的规划。”在他看来,即使现在不拆,由于城市发展太快,艺术家被驱逐也是一种宿命。而驱动这个宿命的,是强大的经济利益和坚硬的法律。
“洼地”造就艺术区
2004年,由于798拆迁传闻,艺术家们开始在周边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这一大片艺术区,正是那时围绕着798而兴起的。李象群称,“这是一种向心力,这里有798,有中央美院,有大片使馆区,靠近机场,使得这片区域文化氛围很浓烈,而且国际化程度高,这是一个交流、展示的好平台,这里存在很多机会。”
此外,已成为创意产业园的798,租金已经涨到每平方米每天三到四元钱。但2008年,当创意正阳艺术区在附近的金盏乡建好之后,画家刘晓东从798搬了过来,“每平米每天0.9元,200平米就是180元一天。”而刘懿的008艺术区的租金更为便宜,“每平米每天0.5元。而且它的租期长,当初与承包商约定的租期是30年。”
除去低廉的租赁价格之外,这里的库房也是艺术家们看重的因素。李象群称,“世界很多其他艺术区,都是在原来工业用地上发展起来的。因为都是大厂房,空间大,稍加改造就能成为很好的工作室。”刘懿说,当初选中这块地方,也是因为“这里是物流区,都是摆放货物的大仓库,应该不会被拆迁”。
这样大空间、低租金的地方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了,昂贵的租赁价格也让艺术家们望而却步。
金盏村的村民和村委会显然乐意将土地租赁出去。在这个城乡结合部,交通便利,村民们早已不靠务农为生,他们进城务工,并把房屋出租出去。与其地段相近的商品房,二居室的租金大约为2500元,但村民宅基地的老房,不靠马路的,租金约为800元。《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机走访了几家准备出租房屋的村民家,其中一间条件比较简陋的卧室,约20平米,租金为每月180元。
这与城市形成了巨大差价。同时,这些盖在集体土地上的大仓库,除了艺术家,几乎无人问津。刘懿租下的这个大库房,每年的租金合计64000元。这对长店村的居民而言,是笔不小的收入。
多数艺术家知道租用集体土地做工作室是违法的,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刘懿称,“我看到开发商方面,也一直在寻求政府的支持,虽然没有得到书面上的首肯,但也确实一直在努力。”
008国际艺术区开幕典礼时,金盏乡领导悉数出席。去年10月前后,金盏乡党委副书记李杰民对媒体表示,008艺术区作为该乡艺术家比较集中的园区,当地政府会创造更好的环境,让更多艺术家来此发展。他说,当年土地违规出租现象比较普遍,大多是闲置土地或建筑用地。为农民增收,只要所建房屋不影响公共、他人利益,乡里并不会强行禁止,而是暂时保留。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炳荣和刘湖北曾经分析过此类“非法流转主体的利益博弈”,在集体土地非法流转的过程中,“对农民而言,处置权在自己手中,有完全权利并获得更高的土地出让补偿;对购地商而言,减少了程序,节约了成本,利润更高;对政府基层组织而言,从中协调可以赢取数目可观的劳务费,几乎无任何风险”。而这样的利益分析毫无疑问使得农民、购地商和政府基层组织都倾向于让土地非法流转。
征地后的利益重组
如果不是朝阳区政府启动土地储备,艺术家和村民们的租赁关系还将继续下去。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室一份论文表明,从2000年开始,不仅是近郊,北京远郊也开始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大量土地使用性质开始变更。这种变更,从城市中心逐渐向外围扩散。
在如今的长店村,“统筹城乡一体”的标语随处可见。一些手续齐全的村民们已经开始到金盏乡政府拆迁腾退办公室领补偿款。《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长店村村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村民宅基地房屋补偿标准为6400元/平方米,艺术区房屋无合法手续,对房东的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总共补偿1080元。
金盏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金盏乡的楼梓庄村和曹各庄村,是金盏金融服务园区先期开发区域,该项目总占地190.47公顷,规划建筑规模144.87万平方米。 而朝阳区东三乡土地储备项目,共涉及3个乡18个行政村,总开发体量约为10.26平方公里。
据长店村村委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这片地区以后将“建成一个能住10万人的小区”,所有村民将以每平米4500元的低价“上楼”,“从此就是城里人了”。
目前尚无法预测这块土地能够拍出怎样的价钱,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而此处经开发之后能够给当地政府带来的财政,更是无法估量。
而此前,由于这些曾经是用来农用的集体用地并未申请更改土地用途,因此均不用给地方政府缴纳其营业税收。
研究者朱东恺与施国庆曾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村一级经济组织得25%~30%,农民只得5%~10%。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的沈飞和朱道林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分析了全国35个地方的农村土地从征用到出让的收益分配关系,其中北京的收益分配在35个地区中最为失衡,政府和农村集体的收益分配比例是46.6比1,而中国的平均数据是17.4比1。
对集体土地的补偿价格仅为每平米1080元,即使按照租给刘懿的0.5元每平方米每天折算,这也仅仅是5年的房租。但村委会,甚至是金盏乡政府,都没有可能与朝阳区政府讨价还价。这是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工作室,本身就是违法的。
2004年3月,《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的内容。
《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金盏乡这些出租给艺术家的土地,没有经过上级政府审批。
这些冰冷的法律让艺术家陷入了困境。曾经支持他们发展的村委会由于同样涉嫌违法,此刻正急于撇清关系。据长店村村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称,“这都是上届村委会的行为了。而且这些艺术家人脉广,他们要用地,随便找哪个领导打个招呼,村里能不批准吗?”
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此刻也称,对于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民间自发设立的艺术园区,政府暂不监管。遇到拆迁问题,只能服从相关规划部门。★
|
|
现有评论:0 [查看/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