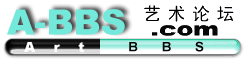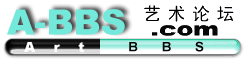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08-02-04 09:45:15
□ 阅读次数:4591
□ 现有评论:0
□ 查看/发表评论 |
|
|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一般历史学的当代美术史
文/高名潞|油画/米娅
|
历史的意义
1.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有了那么多的美术史书,却没有一本当代美术史,而且任何一部美术通史也从不写当代。难道当代美术史就那么不值得我们这许多中国美术史研究者去关注吗?这里除了客观社会原因外,是否还有史学观念方面的原因呢?
翻开中外早期历史名著,不论是断代史还是通史,均离不开当代。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描述他经历的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78年的希波战争(战争至公元前479年基本结束)。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他生活其间的公元前431~前411年的“当代史”。罗马人塔西佗的《历史》,记述公元69年元旦到公元96年的尼禄和多米提安时代,因为他自称史书的目的是“惩恶扬善”,乃至被人称为“鞭挞暴君的鞭子”。我国汉朝“太史公作史记,古今君臣宜应,上自开辟,下迄当代”,而且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也颇有修昔底德斗胆评说不可一世的神圣君主奥古斯都和暴君尼禄的勇气。再看被称为画史之祖的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成书于唐末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记述了自传说时代至晚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的史传,本朝画家206人,而唐以前仅163人;它虽有崇古之嫌,但内容偏重及字里行间均流露了对“当代”的着意之趣。而后来郭若虚、邓椿继续断代,均不忘今;郭之《论古今优劣》,邓之《杂说•论近》,都专辟章节评说当代。
曾几何时,中国美术史成了死人史。近现代以来写的中国美术史,无一例外地均写至清末,郑昶、俞剑华、胡蛮、王逊、潘天寿、李浴、阎丽川诸先生的中国美术史均如是。从清末以后,即近现代以来的美术,在美术史中就成了空白,而恰恰在这近一个世纪内,中国的社会形态、观念意识乃至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脉相承的千年古法受到挑战,传统中国画由独占鳌头跌为偏安一隅的一个画种,当代画坛已面目全非。回视八怪时代,我们不免窃笑冬心、板桥、石涛这些时代逆子也有些酸腐之气了。
这剧变的时代又是复杂的时代,其根本又在于价值观的复杂,传统的“遗少”和西法的“宠儿”在价值的历史天平上上下摆动,胜负难分。于是,盖棺亦不能定论。史学家踌躇了,退避了。
但是,就在中国胆大妄为的当代美术史反衬出胆小怯懦的美术史学的同时,举目世界史学界,仅20世纪以来,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计量分析等等学派,竞相申述史学观和实践方法论。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文化学同步,竟大有以其历史哲学来统摄和引导人类其他学科的雄心!
正因为这样,重提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已是当务之急了
克罗齐的这个命题有两重意思,其中的第一重意思是,历史是当代人的思想的体现。他认为:“‘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例如,当我正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自己撰写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是我的写作思想。”
认为历史是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显示,是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历史已不是编年体的事实连缀,“历史中存在着真实性,这是老一辈历史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但现在显然变成了一个未曾解决——而且在另一些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认识论问题。” 卡尔.波普尔也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
狄尔泰、克罗齐、柯林伍德等人都属历史主义学派,他们的历史哲学是针对过多强调客观的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倾向的实证主义的。这种观点在17世纪由维柯发端,到20世纪由克罗齐和柯林伍德作系统的阐明。他们痛切地感到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两者前进的步伐已经脱节,要以史补救,因为历史不是“剪刀浆糊史”,而是活生生的思想史,而思想正是人类的批判和反思能力。柯林伍德认为史学家在认识历史之前首先应对自己认识历史的能力进行自我批判,他说:“人要求知道一切,所以也要求知道自己”,“没有对自己的了解,他对其他事物的了解就是不完备的。” 确实,你连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都不追问,还有何权力去谈继承或批判前人的历史、去谈历史的本质呢?
历史学家一旦进入对于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宏观的求知欲就使他力求区分自然科学和人类历史的特点。文德尔班将通常意义的科学称为立法的(nomothetic)科学,而将历史学称为表意的(ideographic)科学。克罗齐、李凯尔特提出了普遍的科学和特殊的科学。马林诺夫斯基、卡西尔等人则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区分科学与历史。人对自身(本性)认识的活动被称为文化,是向内的知识,而自然科学则是认识外部世界的知识。不论是特殊、普遍,还是向内、向外,概而言之,历史是人的学问。是关于“自由”的学问,科学则是“必然”的学问。科学是寻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规律的,而历史却是展示人类价值自我实现的赞美诗,它排斥着必然决定论。于是历史更近于艺术。
同时,历史是人的精神史,不同于自然科学,近现代西方历史学主要分为两派。一派强调历史哲学,它亦可称为“元历史”,狄尔泰、黑格尔、马克思、克罗齐、柯林伍德、乃至汤因比都重视历史哲学。反之,实证主义和分析学派则反对“元历史”。分析学派在现代史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大量运用定量和计量的现代科技手段,试图将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否定形而上的判断和体系的建立。
这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科学、自然知识的理解。事实上,强调历史哲学的一派也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其要旨在于要区别人类历史和科学(自然)的本质。在这方面最明显的是,黑格尔、文德尔班、马林诺夫斯基等的历史哲学派要扩大人类的知识范围,认为人类的知识不单单是对外部现象的把握和数理命题的逻辑推论。因此,分歧在于实在的知识和想像的知识。这一问题在近代是人类学之父赫德尔首先提出的,他认为:自然作为一个过程或许多过程的总合,是被盲目地在服从着的规律所支配的;人类作为一个过程或许多过程的总合,不仅被规律所支配,而且被对规律的意识所支配。历史是第二种类型的过程,就是说,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因为它是一种心灵的或精神的生活。其后的黑格尔更强调了这一区别,他认为自然是循环规律支配的,而人类历史却是不重演的,是螺旋式的上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产生的,因为历史过程就包括人类的行为,而人的意志不是别的,不过是人的思想向外表现为行为而已。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从这里来的。但是,黑格尔又将历史源泉归结为理性,而理性即是逻辑,所以历史过程即是一个逻辑过程;而这一逻辑就又回到了与自然规律同样性质的必然规律之中,这种必然则是作为现时的“历史的高峰”时期的人所拟好的。从消极的意义看,必然成为规律,即在观念上束缚着人类创造的丰富性和主动性。但是,从积极的方面看,黑格尔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征服自然的主动性,这正是西方进取精神的根本。黑格尔精通历史,但不是认为历史是高高在上的超脱学问,而是认为“历史并不是结束于未来而是结束于现在”。从他对艺术史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即可看出,较之“象征型艺术”阶段与“古典型艺术”,阶段,“当代”的“浪漫型艺术”处于最高阶段。黑格尔敢于说,在这个高峰阶段,精神回到人自身,人的意识回到“自我”,人藐视现实,凭创作主体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对客观现实的感性形象任意摆弄;“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我们尽管觉得希腊神像还很优美,天父、基督和玛丽亚在艺术里也表现得很庄严完美,但是这都是徒然的,我们不再屈膝膜拜了。” 这显然是近代理性精神。
总之,历史是当代人的思想史;历史不是过往事实的连缀和无判断的实证,而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展现人的心灵生活史。作为史学中的一个领域的艺术史,尽管有不同于其他人文历史的特点,比如艺术史的对象不是文学和故事,而是能一下子激活人的视觉的形象符号,它更多地记录了人类的视觉经验的发展演变历程,但是,艺术史也绝不只是对这些符号的连缀,更重要的是要对其作出解释,而解释角度和对艺术本质理解的差异必然产生不同的艺术史学流派。由此,丹纳才会偏于外部环境,沃尔夫林才会偏于艺术品形态自身(形式风格),贡布里希才会更偏重于文化和观念意识”……进一步说,不论是风格史还是观念意识史抑或心理发展史,艺术史较之其他人文历史,无疑更带有“主观”色彩:无论感性的经验还是超验的欲望都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人自身的影像。因此,近现代以来的哲学家大都很重视美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柯林伍德、尼采、萨特等等都如此,甚至分析哲学家罗素也曾提出“历史作为一种艺术” ,将历史不同于科学的特征归结为艺术性,认为历史应像艺术那样能展现人类活生生的心灵。从这一意义讲,应该说,一切艺术史更是当代史,它不是用文字清晰地展示当代人的思想判断,而是用类似格式塔经验之整合的形式显示当代人的心灵和意识。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还有第二重意思:“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这是命题的根本。自我认识即是判断,判断的主语是个别,谓语是普遍,而这普遍就是哲学。所以,他认为历史与哲学是等同的。“历史在本身以外无哲学,它和哲学是重合的,历史的确切形式和节奏的原由不在本身之外而在本身之内;这种历史观把历史和思想活动本身等同起来,思想活动永远兼是哲学和历史。” 而“思想活动是对于本身即意识的精神的意识;所以思想活动就是自动意识”。
近代“历史哲学”概念(伏尔泰)的提出,反映了传统哲学从对世界奉源的探究(形而上学)转向了对人的认识的考察,体现了从本体论向知识论,从宇宙论向人本论,即从研究客体(包括人在内的对象)向研究主体(包括方法论)的变化。而“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出现,本身即说明了哲学的“现实化”。
历史是思想史,思想即是人类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而这能力正是判断力。那么,历史应当判断什么呢?只是判断事实的真实性吗?历史的事实又是什么呢?不论是自然科学的事实,还是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的事实,当我们说它是事实的时候,其中已经包括了我们对它的认识。这种认识途径在物理学那里是依靠实验、观察、测量得到的,但在历史学那里事实之可测量的机会已经极少,而在艺术史那里就几乎根本无法准确测量。我们只有依靠经验的“体验”、“回忆”和现有知识去解释和判断,而即使是对前人的记述,我们也经常是将信将疑,希望获取那个时代的更权威人士的记述,来进行验证和补证。建立在这种怀疑基础上的正是人的创造性和人的文化的丰富性,它使还历史本来面目始终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历史由此就更多地说明了今人的面目。所以,对以往的揭示就必须站在今人的出发点上,历史学家不可能超越自身和时代的经验与理智,他们的经验和学识必然受到特定的文化圈、集团(社会集团、科学集团)兴趣、道德标准等诸规范的限定。这种规范使人不断地回首往事,又以前人的训诫规范着现实的人的生活。同时,人类的创造又在于对这种规范的超越,因为人只是历史,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当具体的人对其时代及历史的“事实”进行了试图超越的审视后,也就为自己和现代人作出了新的展示与预见。这时,他对历史就提出了新的解释,而这新的解释就是他的创造。天才在于其不可重复的创造,他自己也不能重复。因此,过去与未来在现在汇合。在我们眼中,当代是个“焦点”,而这个焦点向未来的转移,正在于当代人“准确”而令人信服的判断之中。
2.远的历史和近的历史
我们谈到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时,当代的意义是指思想、意志和人的认识而言,排除了时间的观念。而这里的“远”与“近”则是指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人类历史相对于自然发展史只是短暂的一瞬,人类的文明史则更短,而人类具有“历史意识”更是晚近的事情。
当希罗多德第一个用“history”(来源于希腊文iotopia)即“历史\"这一概念时,其含义是求知和真理;他对于“过往”提问以求获取真知,于是他有问必记;资料是他的真理的佐证,而他的真理则是希腊时代的知识学。对于希腊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只是过程,是流逝的事物;世界不存在已知的前定必然。于是,他们对世界采取接受的态度,把它变成确定的知识,并以获得的知识去控制历史中的变化,控制人自身的命运。而东方古代文明则将世界的变化系定在一种已经设想或接受了的结构之中。若从历史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必然历程的角度看,希腊人是反历史的,东方人是重历史的。但若从历史只是编年、是等同于自然科学的考查和认识的角度讲,希腊人又重历史,而东方人则是反历史的 。比如,将人类作为自然生物进化史的赫胥黎的学生赫•乔•韦尔斯就说:“玄奘和希罗多德一样,极其好奇而轻信,但无后者的史学家的细致感,玄奘从来没有路过一个纪念碑或废墟而不追问他的传说故事的。中国人对文学的道貌岸然的风格,也许阻碍了他详细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旅行,谁是他的侍从,他怎样住宿,或他吃些什么,他如何支付他的费用等等历史家所珍视的细节,但是他把一系列照亮过这时期中国、中亚和印度的闪烁的光辉昭示了我们。” 正是希腊人对认识、知识的注重,反而使他们感到了知识的局限性,于是即借助于诗歌展示人类渴望获取自身命运发展的必然规律的愿望。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诗歌要比历史更科学,因为历史学只不过是搜集经验的事实,而诗歌则从事实中抽出一种普遍的判断。
尽管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过单纯求知的史学之不足,但真正借艺术的方法去弥补它,还是近代以后的事。因为只有到了启蒙主义时代,西方人才真正自觉地将人的历史和自然
的历史区别开来,将认识和人性统一起来,虽然不免过于诗意和浪漫,但拓展了历史学的思想范围。历史学在认识自身,反思前人,认识他人。世界史的煌煌巨著相继问世,各种专门史不断开辟。人类的活动过程和空间延长了,拓宽了。而化为历史的艺术和化为艺术的历史,也不再是过去的对事实的力不从心的单纯记载,而是当代精神的生动流露了。如歌德在批评曼佐尼过分强调史实时指出,“如果诗人只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莎士比亚走得更远些,把所写的罗马人变成了英国人。他这样做是对的,否则英国人就不懂。” 这是多么自如的历史观!而历史的延长线即在这自如中缩短了。远的历史变成了近的历史,远去的时间成为近人的体验空间。人类的诸领域的研究与体验都与新的文化生活联在一起了。
这种远近相融的史学并非出于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文化变革意义的功利主义,即清楚地看到认识历史与建树今天和未来文化的关系。即便是历史学中的似乎是纯粹知识学的一面,也离不开今天人类文化的大整体结构。比如,我们在解释仓颉造字这一远古历史事件时,除了运用现代考古发现的佐证外,还要运用现代人的思维方法和解释语言去体察这一事件,决不可能还用汉人的“依类象形”或唐人的“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之类的话进行重复又重复的解释,或者至少也要对这种古老解释进行再解释。这就是新的文化符号的创造。
时代的悠远和事物的泯灭使历史日益成为更远的历史,文化阐释亦带来符号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历史学家往往面对的是符号而不是实物,而实物也逐渐变成了符号,如彩陶和青铜器,于是历史学日益专门化了。但是,如果历史学家不具备构造其解读阐释远古历史的框架的本领,那么他至多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考古工作者,绝对成不了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在创造结构的时候,进行着淘汰和挖掘,正是这种淘汰和挖掘完成了历史的接力。而淘汰和挖掘又是为新的价值观念所决定的。比如,汉代对先秦诸子中影响平平的孔子学说的挖掘,使孔子一跃而为千秋圣人;同时,也淘汰(罢黜)了其余百家。倘若汉代独尊他家,大约中国也非今日之中国了。因此,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研究时,他不仅仅作出因果判断,还要作出价值判断,只有作出价值判断,才会更明确因果关系。一旦对历史作出价值判断,历史也就具有了当代意义。因为,单纯因果关系的历史是必然论和历史决定论的被动循环的历史,而价值判断的历史则是人寻找规律和展现控制社会与自然的意志的历史。于是,远的历史就不仅仅是超脱的由一个必然性的链条连接的诸事件,它与近的历史连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远的历史与现代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息息相关,而近的历史也在价值观的选择中被淘汰和弘扬,从而逝去成为后人的远的历史。
因此,远的历史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史料价值,同时更包含着丰富的人类经验的价值。
当我们在写近的历史即刚刚逝去不久的人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进行着价值判断。我们在淘汰和弘扬,其物化形态成为后人的研究史料。它具有这一时代最重要的史料价值,后人在研究以往一个时代时,必须研究与这个时代中某人某事最近的史家的记录和评价。研究南朝画家必得看谢赫《古画品录》,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必得先看布克哈特的名著。
我们绝不会因为谢赫对顾恺之有点“偏见”而贬低其史料价值,恰恰相反,它迫使我们去寻找更多的经验特别是相反的经验去丰富这一历史人物。在寻找中,我们体验着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撰写当代史,特别是撰写生活于其中、并亲自参与活动的历史,将会为后人留下最为珍贵的史料。然而,当时人的研究和当时人的历史也终究要沦为被研究的对象而成为历史“史料”。恐怕正是这样一种“悲哀”,导致了我们众多的美术史家轻视当代史的思想和心理根源。
就历史的发展和历史家的局限性而言,任何历史著作都是不完美的。布克哈特和汤因比都想写包罗万象的断代文化或人类文化史,但在后人眼中也都受到了史学家思想和客观环境的局限。历史学家永远不会成为高高在上的上帝,不会成为统摄古今、站在世界之外观看人类的永久的裁判者。他从现在的观点观看过去,从自己的观点观看周围和自己的文化,其观点只对于他及与他处境相同的人们有效,因为这种观点体现了他自身的价值。我们不能设想唐代可以有一部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更好的绘画史,因为这更好的观念属于今天的而非张彦远的时代。唐人在努力使自己成其为唐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在努力复兴文艺,启蒙主义者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时代的启蒙者。因而,现在在它总是成功地成了它所要努力成为的那种东西的意义上,是完美的。所谓现在,就是我们自己的活动;我们在进行这些活动,同时也知道怎样活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做了它所想要做的事。
真正令人“悲哀”的,不在于当代终将成为后人反思和批判的历史,故而不易成为永久性的“学问”;而在于,人类的阅历越来越多,竟因而越来越世故了。希腊人以其天真的眼光注视着自身、周围的世界,他们把这肴作镜子和知识。甲骨卜辞、《春秋》、《左传》朴素地反顾着自己的脚步。何必等清人章学诚方定论“六经皆史”,当时著六经者已经在很努力地完成着自己的历史。人类,特别是我们的民族现在太“成熟”了,“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既然我们想使自己的时代成为这一个时代,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对自身和这个时代给予更大的关注呢?
诚然,我们很容易溺于情感冲动和浪漫幻想,成为后人嘲笑的肤浅对象。因为,无论你是否愿意带有集团色彩或个人感情好恶,你都摆脱不了相对于后人来说是“近视”的时代文化的烙印,即“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是,为了认识我,我不能超越我自己,“正像我不能跃过我的影子一样”。历史知识的目的正是在于对自我、对我们认识着和感受着的自我的这种丰富和扩大,而不是使之埋没。当然,这里的我,并非狭隘功利主义的“自我中心”。我们不能歪曲事实,不能不正视这一时代的多方面的“自我”,并将它们在舞台上的表演客观地描述下来。但是,要求历史学家毫不偏袒他著作中所叙述的冲突和斗争的某一方,并无必要,正如伯特兰.罗素所说:“一个历史学家对于一个党并不比对另一个党更偏爱,而且不允许自己所写的人物中有英雄和坏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如果这会使一个历史学家变成片面的,那么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去找持有相反偏见的另一位历史学家。” 当然罗素所指的历史是一般的政治、军事的历史。艺术史中可以说不存在对于英雄与坏人的褒贬。但是,它却仍然注入了对于某一风格、形式、流派、思潮、运动的偏爱,从而也就注入了对某些艺术家的偏爱。因此,艺术史的偏向更多的是价值意向的,而非宗派倾向的。
从全部历史的意义上讲,一切近的历史或当代史都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历史。历史是不断地被证伪和试错的过程,是自我批判和检验的过程,这是卡尔•波普尔的历史理论。由此,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从这个角度上讲,他认为历史无意义;然而“历史虽无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 。这里前一种“意义”是指必然性和自律性,后一种“意义”是指创造性,而正是基于创造的欲望才导出历史虚无的观念。波普尔并不认为他的理论是不可知论,也不承认自己是悲观主义者。相反,他崇尚自由竞争、人道主义,反对权力政治史。他反对历史决定论,至少有一半是基于此。艺术史中难道就没有这种类似权力政治的现象吗? “我们不必装作预言家,我们必须作自己命运的创造者。我们必须学会尽力把事情做好,并且找出自己的错误。当我们不再以为一部权力史是我们的裁判员,不再为了想到历史是否将来要为我们辩解而担心的时候,或许我们有一天能够控制住权力。这样,我们甚至还可为历史辩解。历史是迫切需要这种辩解的。”
这样,我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向历史并向自己提出问题:我们为自己、为人类做了什么?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我们认为现代人类应有的认识水平和价值标准?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是人类今后历史中永恒的真理,但我们是否至少为这个时代的人所理解的真理而进行奋斗了? 无人责问我们的良心和行为,除了我们自己。
当代历史是对所发生的一切创造性行为的描述和解释。于是,它已经是对判断的一种判断,对认识的再认识。因为,当史学家对材料进行清理和分类组织时,就已经在向它们提问。布洛赫说:“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他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面对这些证人,他将首先寻找出一、二个最关键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一旦确定下来,就将是全书结构的主要纵线和横线,由它们组成大框架。它们又衍生出诸多小问题,从而使这一框架丰满起来。历史学家工作的好坏同提出的问题质量高低直接有关,而问题的质量高低又与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和对当代的认识和体验直接有关。在这里学识及思想深度首先是以问题的形式而出现的。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提问的哲学意义,这一点在波普尔的证伪试错理论中论述很充分。而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模式中,非常规的范式的滥觞和确立也始终包含着“问题”。
进一步说,史学家及同时代的史学家群本身就组成了“问题”,他们处于“问题”之中。他们将是下个阶段的史学家的直接裁判的“问题”。相对而言的解决问题或者说对某一阐释的认可总得需要一段过程,即便是在库恩所说的非常规的变革时期,各种价值观的升降沉浮也总得有一个完整的发生发展过程。过程一旦结束,人们似乎就可以理性地加以批判或弘扬,即“盖棺定论”。通常,对于刚刚逝去的历史,人们总是怀、有另辟蹊径的心理,而另辟蹊径的实践即在裁判上一个“问题”的前提中展开。历史就是由不断地提出和裁判问题的过程组成的。当然这决不是一种物理过程,而是一种人类的生命力扩张和沉积的过程。但是,问题的解决程度并非与时间的长短成正比,恰恰相反,年代悠远,使歧义披上了神秘的色彩,而死灰复燃、“复古开新”又会使“解决”过的问题重成疑点。
由于视野、经验、情感等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史学家对自己的当代史很难作出恰如其分的裁判,因为他本身即在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人。正如一个法官判决他的儿子一样,总是不容易恰到好处。因为他不能冷漠,即使苛刻与严厉,也很可能是感情的另一极端。所以有人说,历史学家在历史的伟大审判中,必须为裁判作准备而不是宣布判决。因而,近的历史往往较之远的历史更难,它时时受到即将到来的判决的威胁。但是,如果把它看作只是认识自己和反思自身的记录,那么,却又正如马克思所言:“我说了,我拯救了自己。”
历史学的标准
1.述而不作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历史
从历史只是桩桩事件的连结这一消极层次上理解,它是无意义的。如果从历史是人类不断创造展示其生命力的过程和阶段的积极意义看,它又大有意义。那么,怎样才能深刻揭示出这些意义呢? 换句话说,历史学的标准是什么呢?不容置疑,历史首先得有众多的事件、人物等史料,而这些史料对于治史者而言多是间接的,它散佚在前人的著述中,需要史家花费大量精力去搜集史料,而搜集史料又必得对前人的成说和著述有所了解,于是掌握史料本身就是掌握知识的过程,于是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不言而喻的标准就是博闻广记。然而,这是低层次的标准,是一般的史学工作者的标准,它是并不能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标准的。
首先,资料并不存在客观性。从数量上看,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所有史料都是经过淘汰和选择才保留下来的,它们也是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偶然幸免者,而更丰富的地下史料还有待发现。所以,单纯地追求大量史料的史学目标,本身并不是客观的,绝对充足的史料就像绝对的真理一样,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其次,资料的归纳整理过程就是理论形成和理论渗入的过程。史料本身并不说明任何立论的正确性。因为,真理不是来源于纯粹的经验,、当我们对任何一段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时,成见已先入为主,即理论已先于陈述。对中世纪艺术史的评价的反复,中国长达千年之久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艺术流派的沉浮等大量史学现象,都证明了史实本身的客观性是与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变化和转移密切相关的。
一种错误的看法(这种观点目前在美术史学界很盛行)认为,掌握了越多的史料特别是独家史料,就掌握了这段历史或者这个人物的历史的权威地位。在有些人心中,史料完全是累加起来的一个个死的证据,当他们积累到一定的数量,特别是超过了别人的时候,就掌握了真理,因为他们的立论是根据众多的史料归纳出来的。在科学哲学中,有人将这种观点称为朴素的归纳主义者。“所有的归纳主义者都主张:在科学理论被证明为正确的限度内,它们是在经验提供的多少可靠的基础上借归纳法的支持而得到证明的。” 也就是说,归纳主义者(即史料至上主义者)将立论建立在观察和获取的间接知识的基础上。罗素以“归纳主义者火鸡”的故事讽刺了这种看法 。
所以,“归根结底,历史学家的资料和他的结论没有差别,他一旦作出结论,这些结论就变成了他的资料,而他所有的资料都是他已经作出的结论,资料和结论的差别是由已解决的问题与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差别所引起的一种暂时性差别,这种历史判断就是结论。”
柯林伍德讽刺那些只知辑录史料,对史料如数家珍,然而毫无思想的史学为“剪刀—浆糊历史学”或“剪贴史学”,这种史学只知排比过去现成史料,再缀以几句本人的解释,仿佛史学家的任务就只在于引述各家权威对某个历史问题都曾说过什么话,都是怎么说的;换句话说,“剪贴史学对他的题目的全部知识都要依赖前人的现成论述,而他所找到的这类论述的文献就叫做史料” 。席勒称这类“学者”为“混饭吃的学者”,“这样一个人的雄心就是要成为一名尽可能狭隘的专家,而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话虽尖刻,却极鞭辟入里。那些只知抄录史料并将其编排在一起的工作虽然为史学提供了条理化的材料,但它却不是历史学本身,因为它没有经过人们心灵的批判、解释,没有复活过去的经验,它是单纯的“学问”或“学力”。
史学有史学的义理,既不能用考据本身代替义理,也不能以考据的方式讲义理。只有通过思想,历史才能把一堆枯燥冷漠的原材料形成有血有肉的生命。柯林伍德将这种科学的历史归于培根之后,而前培根的历史则被他称为历史编纂学。我国古代和现代史学家也曾悟到史学的义理。如章学诚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政典也。”“史之所贵者义也。”他还举孔子作春秋为例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 但不可否认,古史之义理,主要是以考据和辑录的方式撰写的,虽然可以从其“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的史料描述中“窃取”其义,但毕竟未明确自觉地以批判的思想入史;相反,官修史学专意于承前代遗训。而孔子“述而不作”一语,则道出了传统史学的根本宗旨。
如果将史料学和历史哲学作为史学的两大部分,那么中国传统史学则主要是史料学,是“断烂朝报”。近人“六经皆史”之说,乃是以经补传统历史哲学之空白的自我解嘲。
但并非没有例外。中国古代绘画史中,唐张彦远囊前人品录而作的《历代名画记》被称为画史之祖,是书虽远比不得《史记》之恢宏,然而在绘画史著中确有《史记》在中国史籍中之地位。诚如近人余绍宋所言:“是编为画史之祖,亦为画史中最良之书,后来作者虽多,或为类书体裁(如画史汇传等——引者注),或则限于时地(如时下专史一类——引者注),即有通于历代之作,亦多有所承袭,未见有自出手眼,独具卓裁。” 后人之书不如张氏之处,并不全在于张氏史料齐备。固然,第一部通史,其材料价值是首要的,如《史记》一样。但从其书法而言,张氏很重以论贯史,虽然今人视其论,不免迂腐,但他对于画的本质(主要从功能方面讲)、画的流脉、画的风格、画的制作技巧以及考订著录等均一一涉及,并试图构造一个框架(虽然我们现在看来这框架有支离之感,缺乏科学的系统和内在有机的联系)。
可惜,后人郭若虚、邓椿、夏文彦等皆步其体例,少有创造记传的延续。至有清一代,著书甚伙,盛行巨著,即如张丑、卞永誉、吴荣光、吴岐、高士奇等人之书多为著录之作,到敕撰《石渠宝笈》和《佩文斋书画谱》则达到顶峰。近人黄宾虹、于安澜、俞剑华诸先生也于此多有巨著,为丰富中国画史资料卓有贡献。但是绘画史亦因此而走向单纯的“述而不作”的史料史和著录史,遂造成千余年来竟没有超过《历代名画记》的绘画史著作问世,同时,在浩如烟海的绘画史著中竞没有一部论史的著作。可见传统的史家们争先卷阅可靠全面的史料,而对于绘画与人是什么关系却麻木到了何等地步!虽然,西学传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对绘画史研究产生了影响,但并未扭转这种现象。另一方面,历史哲学又被理解为简单的阶级分析法,或者是简单地以唯心与唯物、非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为标签的庸俗社会学。在结构和层次角度方面仍很单一。
因此,扭转这种只动手不动脑的传统史学观和庸俗社会学的史学观,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论撰写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已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而这方面的首要前提则是必须加强历史哲学的研究。不清楚“为何写”,尽管采用最新的“怎样写”的方法也仍是殆同书抄。
所以,我们解放史学家的思想的途径应该首先由复述史料进入复活历史,然后进而创造历史。
今天,西方各种史学方法的传入为我们的史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领域,我们可以将文化阐释学、图像学、符号学、社会学、计量学等各种方法引入艺术史研究。但是,无论何种方法,其有效价值都只能在对特定区域和特定文化时代的艺术史的研究实践中实现。这里,“特定”二字要求史家必须具备许多特定的条件,至少要有解读特定艺术形态(时代的、民族的)的本领。于是,其方法也就必然是特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借鉴来的方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方法。所以,借鉴方法还是为了寻找“特定”意义;在寻找“特定”意义的同时,也创造了特定的方法。
总之,历史学的标准首先是在我们的脚下,而它的实现则视我们头脑中思想的开掘程度和生命扩张力的强度。
2.经验的描述和理性的阐释
事实上,关于一部史著是否“客观”、“准确”、“深刻”等等评价标准,除了与前面所谈的历史哲学的深刻性及其统摄下的史料的丰富性有关外,也与著者的认识中的经验成分有关。因为历史首先是一种认识活动,而经验正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狭义的经验仅指直接感官经验,广义的经验包括感官印象和内省两个方面。在历史研究活动中,这两方面即体现为情感倾向和对过往事实和经历的带有总结性的直觉把握。如果历史学家没有这种个人的经验之光,他也就不能观察和体验他人的经验。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在艺术的领域里,如果没有丰富的个人经验就无法写出一部艺术史;而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系统的思想家就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部哲学史。”
历史学家正是凭借他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个人的情感意向,选择着描述历史的概念和语言,甚至选择着历史事件。这里,他既排除着以一种冷淡态度来进行超验的“永恒性建构”,从而将活的事件和记述看作单纯的知识而非价值判断的原材料,也排除着单纯的感情和欲望的干扰。历史是激情的历史,更何况我们深怀激情地参与了历史。但是,如果试图将历史写成激情,那么它就成为诗而非历史了。我们的同情是理智的和想像的。我们是以一个体验者的身份去体验各种派别和倾向的人和事件,这体验依赖于此时历史学家的诸种经验。没有体验的历史是枯燥干瘪的历史。但是,对某一方的倾向性不应以激情表现出来,而应以深刻的分析和自我批判精神去表述。一旦历史学家摆脱了自我中心的世俗情感,即进入了认识和感受着自我的丰富和博大的“我”的境界,从而也就进入了理性的阐释的层次。
历史学的理性的阐释,主要是指历史框架的重建,将历史学家经过体验的有个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编排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是,如何建构历史的结构,则首先遇到到底按照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还是按照先验主义的历史必然论去构架历史的问题。前者的历史被波普尔称为无意义的历史,这种历史主张先“搜集资料,再建立结构(按因果把它们联系起来)”,这即是丹纳的史学观。它过多地强调了客观事实对判断的衡量和检验,然而这些事实并非将要发生的,而是以往发生的,于是,用过去的事实检验现实经验无疑就背离了人预测和控制未来历史的本能和愿望,从而排斥了人的目的性和历史学的目的性。而先验主义的历史必然论则主观虚拟一个必然的线性结构,然后借助经验将“事实”塞进去。
上述两种历史结构观念分别基于洛克的经验主义和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理主义的认识论。它们作为近代认识论的代表,都将古典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转为发掘人类知识潜能的认识论了。但此后的认识论,特别是从康德开始,将自然的客观性和意识的主观性对立起来。此后的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哲学则试图解决这种二元分立的难题。比如新康德主义的文德尔班提出以价值论代替认识论,判断是一种价值形式,即一个判断之所以为真,不是通过事物或客体的比较而来,乃是由于直接经验感到有责任去相信它 。这里“责任”显然是经验产生的动力因素,通过它超越传统的主、客观对立的认识论之谜。文德尔班的价值论观念确实可以启发我们在著史时对经验的既尊重而又超越的把握,即注重一种对本质的直观的过程。
此外,从文化的角度看,绝对的个人经验是不存在的。比如,当代发生的事在当代人心目中总有某种趋向性;即便看法相异,但在把握事物的意向方面总有一定成分的一致性。同时,当我们在体验和描述着某阶段内的历史时,此阶段外(之前、之后)的有关的事件和因果都潜伏在头脑中,并不断地干预对此阶段内的历史的描述。因此,历史描述中的经验总有先验的成分。这些先验的成分是由史学家的知识、思想、对历史事件的了解程度所决定的。
在先验之光闪耀时,它可能是以“悟”的思维形式出现的。它使我们洞悉历史的内在联系,常常提供给史学家不同凡响的判断。但是,这判断应当是清晰的,而不应当是似是而非的,它应当基于直接经验和价值标准的历史目的,而不应皈依上帝所缔造的神秘而不可追问的永恒规律。
由于理性的阐释的要点在于结构和内在有机联系,所以它排斥史料的支离和具有情感色彩的心理因素的干扰,于是对现实,特别是史学家正在面临的现实采取超脱的姿态。但是,超脱并非回避和畏难,而是为了自我批判和内省。
没有经验的描述和情感的体验,就没有历史的个性和动力。没有理性的阐释则没有历史的延续性和严密性。科学的历史就是经验的描述与理性的阐释的结合。
注: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历史有意义吗?》,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出版社1986年版。
《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2页。
《历史作为一种艺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90页。
参见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参阅《诗学》第九章。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历史作为一种艺术》。
《历史有意义吗?》。
《历史有意义吗?》。
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这只火鸡发现,在火鸡饲养场的第一天上午9点钟给它喂食,然而,作为一个卓越的归纳主义者,它并不马上作出结论。它一直等到已收集了有关上午9点给它喂食这一事实的大量观察。而且,它是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这些观察的:在星期三、星期四,在热天和冷天,在雨天和晴天,每天累加陈述。最后得出结论“每天上午9点给我喂食”。在圣诞节前夕,当没有给它喂食而是把它宰杀时就毫不含糊地证明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
《历史的观念》第257页。
《文史通义•内篇•易教》。
《书画书录题解》。
参见[美]L•W•贝克:《新康德主义》,《近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资料》,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
现有评论:0 [查看/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