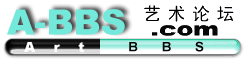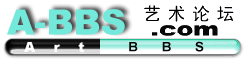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09-07-10 12:01:41
□ 阅读次数:18002
□ 现有评论:0
□ 查看/发表评论 |
|
|
北京之外,谁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副中心?
新周刊
|
当代艺术副中心之争一直争论不休。
艺术副中心并非艺术陪都,深圳、重庆、上海及郑州,都有各自发展的赶超之举和奔跑态势。共识产生于艺术是城市活力的一部分。
在经历了“科技立市”、“旅游立市”、“贸易立市”等等城市战略后,中国的城市把眼光瞄向了“当代艺术立市”上。与前几种战略不同的是,艺术战略跨越了不同地域和城市文化,一下把性格各异的城市拉到同一个横截面上来。
北京之外的城市,谁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副中心?当代艺术中心的价值,既在于要拉动艺术品的“票房”,又要拉动城市本身的文化经济地位。这意味着成为“艺术副中心”至少需要两方面的努力——城市规划者的引导和艺术家的积极响应。
既然是“规划”,必定要求城市的自身条件与“艺术中心”吻合,至少具有“跳一跳能够得着”的潜能。中国有大批城市具备成为当代艺术副中心的可能,而能否最终成为副中心,首先要看的不是谁更接近中心的标准,而是要看他们自己的欲望有多强烈。
城市投奔艺术,并非假想的热情。这考验领导者到底有多英明,尤其对于缺少建设艺术城市经验的中国城市领导者,“尝试”的机会成本有多高?
◆西部艺术副中心:重庆
号召力:涂鸦街/四川美术学院/坦克仓库/501基地/罗中立/《当代美术家》
在重庆艺术家群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你去北京了吗?”
当然,除了艺术圈,任何北京之外的城市,各种职业各色人等,在任何可能的环境下,都可以在互问前途时扔出一句:“你去北京了吗?”而在重庆的艺术圈子里听到这几个字,多少会让重庆艺术人心里五味杂陈一下。
“重庆从上个世纪末才真正成为西南艺术的重镇。因为有了收租院,出现了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高小华……以及后来的一大批艺术家。早期的伤痕美术就出现在重庆,它正好和‘文革’的结束作一个对应,这种与社会的对应使四川美院的艺术开始崛起,后来还有乡土画派、野草艺术事件等一系列的延续。所以直到今天,重庆仍是大量培养艺术家的地方。”《当代美术家》主编俞可对于“重庆作为西部艺术家输出的一个重镇”,是肯定的。
重庆本土艺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生产艺术家的地方,但是,除了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其他的艺术环节都基本缺失。
重庆之于全国,与中国之于世界相似——需要通过“出走”,去与外面的展览、画廊、批评家一一对接,才能获得成功的认同。重庆的艺术家们认为问题包括很多方面,首先,这个城市没有美术馆——重庆唯一的美术馆现在嫁接在四川美院,这导致艺术的展览机制单一;其次,这里也没有正规的画廊或其他艺术机构,艺术品的市场机制因此很难建立;尤其重要的是,因为没有与公众互动的艺术空间,因而大众也缺少阅读艺术的习惯。
现实是,重庆的本土艺术在展示、流通和收藏等各个环节显得薄弱。尽管四川美院是一个艺术人才的集散地,“但这里就好比一个种菜的地方,而批发商则全部来自其他城市。尽管今天的艺术家说到卖钱,大家的兴趣都很大,但资本的流通没有在这里完成,所以重庆基本上是初级市场,或者说它还没有达到一个终端。”俞可比喻。
重庆的涂鸦街,曾被多方关注与讨论。“它与西方真正的涂鸦是有很大差异的。第一,它是政府行为,与艺术家的自我创作、自我冲动、自我发泄和自我表达没有任何联系。第二,它的形成过程是:从网上下载稿子,再让棒棒进行高空作业,这种涂鸦的方式应该算是项目工程,而不是艺术创作。正是因为这两点,它也区别于欧洲和西方其他地方的涂鸦模式。或许我们说重庆创造了一种全新涂鸦模式,让世界大吃一惊。”俞可坦言:“政府在一种假想和热情中,成就了让人惊奇的艺术形式,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它和西方的涂鸦完全南辕北辙。实际上,艺术家自发的涂鸦在这里是不被允许的——作为一个社区,它没有一个空间给艺术家自由地做这个内容,但政府大规模的装饰涂鸦就受到比较好的对待,它用行政的手段说服老百姓,让老百姓都接受这个事实,让他们觉得涂鸦以后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涂鸦活动和政府的想象合作,成为顺理成章的必然。于是,涂鸦就成为文化产业的催情剂。”然而黄桷坪的涂鸦的确叫国人和老外都大吃一惊:“这么高的涂鸦,艺术家是怎么完成的?”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四川美院是重庆以外的一个地方,它和这个城市没什么联系,重庆整个城市与文化的推进从来不受四川美院的干扰。而让人奇怪的是:四川美院的艺术活动对全国的艺术活动影响很大,它和中国艺术史、整个艺术进程包括其他地方形成很强的动力性关系,但在本土就显得很无力。”俞可举例:重庆市的城市雕塑与四川美院雕塑系的创作没有联系、四川美院的艺术创作与重庆市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重庆市民更没有从“西部艺术重镇”获得好处。“现在重庆有多少人像北京、上海那样观看艺术展览,他们为此做了多少活动?仍然没有。所以我说这个城市与这个城市生长的艺术实际上是脱节的,没有一种直接、必然的联系。因为这个城市从上到下的文化艺术认知,仍然被土生土长的文化所误导,这也构成了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形象差别。”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对职业艺术家的“成功”如何定义,是指学术上的建树还是市场上的叫座。如果是指双赢,那么成功的模式突然简单化了——借助于各种类型的展览,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得以更大范围地扩散,以此来构成影响力,并进入大众的视野,同时也进入艺术市场的流通。
◆华南艺术副中心:深圳
号召力:何香凝美术馆/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华侨城/梁宇
城市的特色及影响构成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城市在区域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一点是深圳文化局艺术处处长梁宇一直坚信的。
与国内其他一些重要艺术城市略显不同的是,深圳的很多艺术活动,都被贴上了“文化立市”的战略标签,并且在最近几年里,这个战略发挥了它的最大能量。
“总的来说,广东的美术馆事业还是运作得比较好的,也是比较成熟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发展中,广东的美术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认为:“深圳的几家美术馆同样值得注意,像何香凝美术馆及其下属的OCT当代艺术中心,一直推动着全国各地重要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深圳画院主办的常规项目‘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和深圳美术馆举办的系列当代油画展与学术论坛也为中外艺术家之间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不过,这两年来出现的新现象还是值得广东美术馆界的同行注意,那就是广东以外的地区出现了数量更多的美术馆,它们的运营资金在加大,运作也更规范、更有力。按照这种势头去发展,如果广东这边的几家美术馆不在资金、人才、运作理念上投入更大的力量,那么广东这边的美术馆势必会被其他省市的美术馆超过,到时候,恐怕优势地位就会不存在了。”
而在深圳之外的“旁观者”看来,深圳的艺术特点,除了“水墨比较多”,还有“复制北京”——将北京等展览模式复制到深圳展出,实际上与当地文化艺术现状没有多大关系。而作为地域的深圳当代艺术,艺术到底有没有本地与外地的概念,其好与坏是否取决于“本地”或“外地”,批评界还有诸多争议存在。
深圳的特殊性在于——它在二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中,和北京、上海一样都是不能被忘记的:改革开放的光辉一直笼罩在这座沿海城市上空,深圳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深圳画苑、何香凝美术馆常年都在积极地组织各种艺术活动。华侨城做得更为超前,它以一个企业的方式而非基金会的方式无偿资助艺术发展,以模仿国内外画作而形成产业的城中村大芬村设计了“大芬美术馆”。
而深圳真的能担起“副中心”的重担吗?到底是艺术为城市而穷忙,还是城市在为艺术而奋斗?
“不能一提文化生产产业化, 政府便撒手不管, 任由市场主宰;也不能因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 而一味地关闭文化进入市场的大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该管的一定要管好, 不该由政府出面办的文化一定要退出。”梁宇的主张显然有利于避免“政府过度干预艺术”的危险,而当代艺术能否在深圳健康发展,同时获得政府最大程度的支持,是深圳成为艺术重镇的关键。
◆中部艺术副中心:郑州
号召力:中原文化/河南大学/萧开愚/郑东新区
在先锋城市们不断地创造自身出路的同时,之前位于艺术“二线”或者“三线”的城市,在没有找到出路之前,“尝试”和“模仿”也不失为务实的方法。
2008年11月,郑州市规划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未来郑州市将朝艺术之都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艺术之都的定位。
这个消息让郑州本地媒体来不及反应——“我们的城市有艺术吗?如果有的话,大概也都是土黄色的吧。”一位郑州的媒体编辑在看到这个消息时,感叹“艺术离我们好远”。
而刚刚公布的2009年河南省艺术高考生人数统计数据显示,河南省艺术考生人数一举突破10万人。按照去年郑州高考有百万考生算,每十个考生中就有一个艺术考生。河南也成为仅次于山东的又一个艺术考生大省。很多学生和家长承认报考艺术类考试是为了“曲线救国”——以求读更好的学校,但至少他们道出了一个现状:郑州市民对艺术的价值是认同的,艺术在普通市民眼里不再是一根鸡肋。
这恰恰提示了在高度信息化的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有认同当代艺术价值的可能。艺术市场的嗅觉是不会放过这个信号的。
“郑州是汶川大地震后第一个来西安推介的城市。”2008年6月初,“欢乐郑州行”在西安举行推介会时,西安市旅游局副局长康立峰感叹地说。“2008年,郑州旅游面临重重困难,我们只有积极应对、迎难而上,才能确保完成各项指标。”郑州市旅游局局长岳俊华表达了郑州推广城市文化的决心和积极的态度,目前仍然以“旅游立市”的郑州,2008年9月26日举办了第十届亚洲艺术节,来自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和中外艺术家,走进了这座人们旧印象中“土黄色”的城市。
◆东部副中心:上海
号召力:莫干山艺术区/苏州河/上海双年展/张晴/陈旭东/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国际画廊业/奢侈品牌与金融机构
寄自上海的绝大部分画展请柬,落款都是“莫干山路”。
莫干山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境内,相传是干将莫邪铸剑之地。而上海的“莫干山路”既没有干将,也没有莫邪,只有大片大片的艺术区,并在此地彼此联络出一张艺术地图来。
过去的几年间,上海一些初成规模的艺术区域都经历了变迁——浦东的画家村因房产纠纷而结束,苏州河畔的艺术家仓库遭遇拆迁危机。而莫干山路的艺术单位们,也正在讨论什么时候改变一下,重新规划或者寻找新出路。
1998年台湾设计师登琨艳最先入驻上海苏州河边的仓库,此后一批艺术家在西苏州河路1131号、1133号仓库等地相继开辟工作室。比邻的莫干山路50号春明工业园区,“拥挤”着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风情各异”的厂房,背临苏州河。2000年5月画家薛松第一个进驻莫干山路50号。短短两年,莫干山路50号崛起为上海最大的艺术仓库群。按照一些艺术家的描述——他们的工作室,有的光线诡异,有的湿搭搭的墙面渗着水,当然也有阳光充足的个案,“可喜”的是,艺术家们各安天命。2002年5月,西苏州河1131号和1133号仓库拆迁,那里的艺术家们和东廊、香格纳等画廊的老板就近搬入莫干山路50号,同时还带来新的一批当代艺术家。2002年另一片艺术仓库淮海西路720号同样因市政拆迁而消失,这批艺术家也于2003年2月相继进驻莫干山路50号。
现在这个原本安静的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上海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区,并且从工业园向创意园过渡。同时它的能量不断“向外”辐射——北京等上海之外的城市,总能听到“莫干山”的声音。
如果以莫干山路为上海艺术区“演进”的标本,可以看出,上海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根据地是在不断地颠沛流离中渐渐汇聚到现在的莫干山路50号,而这又恰恰是其他一些艺术城市所经历过的,比如纽约、北京。只是是否能与其他艺术中心“同途同归”,尚待证实。
相比一些内陆城市,上海成为“当代艺术副中心”的优势非常明显——甚至在很多艺术从业者眼中,“副中心”可以直接替换为“中心”。至少,当代艺术的“天时”和“地利”,上海都具备,唯一不稳定的“人和”因素,正有待观望。
2008年年底,一场关于莫干山路50号改造的圆桌讨论,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始了。陈旭东带着他的“M50/莫干山50号的城市营造”计划,从建筑师的角度阐述了多功能性对于一个新兴地块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它可以让艺术和时尚的氛围在其中自然地生长,而不是硬拉一些展示活动和时尚活动在这里。不管是新的‘双塔’高层办公楼,还是艺术家住宅,都希望从硬件的角度给园区搭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平台。只有人来人往,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氛围产生。地点其实不重要,就像M50,与场地相比,更重要的是有这些人、这些艺术家在。”
如果陈旭东和他的M50计划能够按照预想实现,那么上海相比其他城市,显然多了一些看点和可能性,将它朝着“艺术副中心”更推近了一步。 |
|
现有评论:0 [查看/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