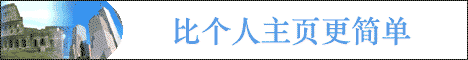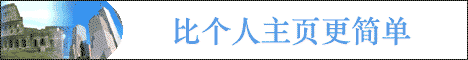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 刊发于《建筑师》
第110期
□ 阅读次数:11170
□ 现有评论:0
□ 查看/发表评论 |
|
|
私人身体的公共边界——由非常建筑谈表皮理论的中国接受情境
唐克扬
|
【概要】本文不打算对“表皮”这一理论现象作面面俱到的梳理与分析,而侧重于讨论表皮理论在中国建筑实践的上下文里所可能产生的意义,除了关注理论自身的渊源与其文化逻辑,本文更感兴趣的是,当表皮理论所倚重的西方社会和文化情境在中国不可避免地变质之后,是否可以仅仅在技术层面上讨论和运用表皮理论,这样做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本文的讨论将围绕表皮理论的一个主要关键词,即(社会性的)“身体”而开展。从建筑师对建筑设计中的公众/私人领域关系的经营之道,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新的建筑理念冲击着社会生活的空间组织形式,这种理念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的社会生活空间组织形式的掣肘。
【关键词】身体 内/外 公共/私人领域 界面/界面确立 [interfacing] 张永和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at no encyclopedic discussion on the surface theory. Instead,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ractice. While most Chinese architects tend to neglec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 in which the Western theories were developed, will the discussion of a generic and timeless concept of the "skin" be able to make enough sense to its Chinese "body"? And what if we examine the surface theory in a pure "technical" sense? The discussion is organized around the key concept "body", leading us towards a sociologic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 Chinese situation. In this situation, elite architects reluctantly deal with the inevitable confronting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territories in their design by dissolving the surface issue in the rhetoric of "interfacing".
Key words: body, inside/outside, public/private, interface/interfacing, Yung-ho Chang.
在这一期《建筑师》“surface”专辑约稿时,众位作者曾经为两个关键词“surface”“skin”的译法作过专门的探究,我个人倾向于将surface译为“表皮”,skin译为“皮肤”,理由是它们最能够反映围绕着surface和skin而展开的西方建筑理论的生物学类比的渊源和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能够反映这两个英文理论术语的语源意义和(社会性的)“身体”的关系。[1]
这种咬文嚼字并非基于历史学家的考据偏好,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有意识的选择。对于围绕着表皮或皮肤的西方建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我首先感到好奇的是,如果表皮或皮肤所代表的“身体建筑学”[2] 所涉及的必不可免地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body,我们是否可以绕过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分析,而停留在“纯粹建筑”(借用一个建筑网站的热门栏目名)的领域内而抽象或技术性地谈论这两个词的涵义呢?如果中国建筑传统对于“身体”的理解本基于一个独特而自为的社会现实[3] ,那么什么又是当代中国建筑师借鉴西方表皮或皮肤理论的基础呢?
两个在概念层面上成为建筑现象的例子可以更好地陈述我的问题:第一个例子是安妮·弗兰克之家(图1)。这所“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独特之处在于很大程度上,这“世界中的世界”是一个逃逸性的,外在“表皮” 暧昧不清的空间,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建筑物理边界的缺席,而是因为暴力与死亡的恐惧造成的心理压力,使得西方社会中的公众领域和私人身体之间的通常关系在这里发生了变形。私人身体——这里的私人身体不完全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构成公共和私人领域边界的最小社会单元——不再向外部世界开放,它惟一的选择是将公众领域从自己的意识中排除出去。但这种排除又是令人不适的,因为向外交流的渴望依然存在——一方面全家人日夜惊恐不安地倾听着抽水马桶的声音是否会引起邻居的怀疑——因为他们无法确认外在世界和他们的避难所之间的物理厚度,生怕藏匿所里的声音讯息泄漏了出去,另一方面,那种缫绁生涯里的对于交流的渴望和由于恐惧外部世界而造成的自我封闭又是相互冲突的。归根结底,社会性的身体依赖社会交流活动确立起它和外在世界的边界,这种边界的确立本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和有明确的文化旨归的社会性感知,既确保自身独立,又鼓励向外交流(图2)。当这种交流活动的正常进行受到干扰时,生理性的身体甚至也会出现心理性的不适,就像安妮日记所描述的那样。[4]
与之相应的中国例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当刘伶裸裎于自宅内,时人颇以为怪,而他的解释是他“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而对于提问题的人他反诘“汝何事入我内?”[5] ——这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文化对于社会性身体与建筑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在安妮之家的例子里,无论安妮一家是否真的忘却了那个世界外的世界,那道边界都不曾消失过,内和外,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清晰区分和对立构成了建筑表皮类比身体表皮的社会学基础。而对于刘伶而言,建筑边界所代表的向外交流的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边界所界定和保障的特定社会空间内的主仆关系,使得主人在他占有的空间中向内获得绝对的权力,可以令生理性的身体扩展到建筑的边界,也可以收缩到一沙一石[6](图3)。而在私人空间之外并不是公共领域,而是另一重同构的由主仆关系主导的社会空间秩序,穿越这两重秩序之间的边界时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建筑空间性质的变化,而是母空间的权力客体变成了子空间的权力主体,每一层级的权力主体而不是客体才有能力获得对于空间的明晰的社会性感知。在这种内向性的社会感知中不存在公共领域和私人身体的鲜明区分和戏剧性的对峙,只是室内颠倒过来成了室外,而对于“大”(公共性)的寻求往往要在“小”(家庭或私人领域)的同构中完成。身体的领域由此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随时都可能由于社会权力关系的变更而改变,或换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性身体中重要的是一种确立界面的动态关系[interfacing],而不是作为界面[interface]的表皮自身。[7]
在概念层面上举出这两个例子并不是想泛泛说明“中西社会文化心理的差异在表皮理论中的反映”一类的话题——我只是想指出,任何“纯粹建筑”的要素都不是不可拆解和卓然自立的,表面上“非建筑”的社会学因素有时候恰恰是改变建筑属性的关键。[8] 进一步地分析,我们看到构成表皮和身体的关系的建筑解读中有两组重要的机制,其一是内和外的关系,其二是由确立界面[interfacing]而带来的深度,或内外交流转换的动态机制,在对应的建筑社会学意义上,第一组关系可以看作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静态空间布局的问题,这一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二元的,基于传统表皮理论的一般语义上的,而第二组则牵涉到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体意义上的身体是如何结构性地、动态地和公共领域发生关系,这和社会性身体的一般性功能有关系,也是在近年理论家对表皮建筑的新发展对传统建筑扮演的颠覆性角色感兴趣的一个主要方面。
回到具体的建筑问题上来,我想就这两组机制分析一下张永和/非常建筑的一些作品,尽管张永和并不曾个别地表现出对于“表皮”的兴趣,通过使得建筑单体和更大的环境或组织——大多数时候这种环境或“组织”在张永和的语汇中等同于“城市”——发生关系,张永和在技术层面上发展出了一套结构性的“表皮”设计思想。虽然这种“表皮”——准确说,应该是建筑和环境的“界面确立”[interfacing]——的思想已经和它在西方理论中的既有语义有一段距离,它却反映建筑师在中国从业的社会情境中,建筑空间里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交流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从而揭示出表皮在中国建筑实践的上下文中可能的意义。
我所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张永和对于“内”和“外”的看法。
张永和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所理解的建筑“不是从外面看上去的那一种”[9],并进一步将这种区分概括为空间、建造和形象/形式的区别,他对许多当代西方建筑师的好恶常常受制于这一套标准[10] 。我们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张永和认为建筑的根本任务是创造空间而不是形象,我们并不十分惊奇地看到,张永和在用“空间”置换“形象”的同时也用“个人”置换了“公共”,从“外”退守到“内”,远离“大”而亲近“小”。当早期张永和相信“小的项目可以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而“体现建筑师个人趣味”时,他所欣赏和笃信的“空间”理念带有一种私人化和精英化的色彩。这种色彩并不完全系之于项目的公共或私有性质,而是以保有私人化的建筑体验为理由,有意或无意地否定了调动公共参与,或说一种自发和全面的建筑内部交流的可能,从而将建筑内部彻底地转换成了一个紧密的被置于建筑师一个人的全能知觉支配下的空间;第二,张永和对“内”的喜好是建立在对“外”的舍弃之上的,当建筑的内部空间和隔断在建筑师心目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时候,当私人经验可以自由地放大为公共使用时,一般意义上的建筑表皮就显得无足轻重,它的社会性就悄悄地被尺度转换中对于建造逻辑的关注所遮盖了。对于更愿意退守于内的建筑师而言,外表皮只是一个语焉不详的遮蔽,是精英建筑师不情愿地和社会发生一点关系的物理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表皮自身的逻辑和建筑内部并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它和建筑外部的城市语境的联络也往往显得特别薄弱——当然,这并不全然是建筑师的问题,而很大程度上出于社会情境的局限。
对于张永和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无上下文的室内设计(不考虑基地问题)和私人委托设计(基地通常坐落在野外、水滨等环境中),上述的情况还不至于为单体建筑的设计理念带来太多的麻烦,我们不妨用这种观点来分析一下他的一个基地情况比较复杂的公共建筑设计,例如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图4)。
在张永和回归中国情境的过程中,这个早期设计所面对的社会问题颇有象征意味。“足不出户的数学家”将一天中的全部活动,即住宿起居和研究工作放在同一幢建筑里的做法是不多见的,乍看上去,这样的设计要求和西方“住家艺术家”[artists in residence]的制度或许有某种渊源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张永和对这种要求的建筑阐释暗合于中国大众对于数学家的漫画式图解那就是为这些潜心学问,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自给自足的“城中之城”的体验。然而,其一,尽管建筑的内部空间单元之间有着丰富的一对一的视觉和交通连接,但它却没有现代城市所必不可缺的公共交流区域,以及一个共享的空间逻辑,数学家的大写的“城市经验”恐怕只整体上存在于建筑师的全能知觉中;其二,建筑师显然认为建筑的社会交流的功能已经在内部完成了,因此外表皮的设计只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它的“一分为三”,即固定玻璃窗用于“采光和景观”,不透明铝板用于通风,铝百叶用于放置空调机,等等,似乎机巧,但却是整个设计中逻辑最松散的一部分,建筑师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座自足的、向内交流的微型城市还有向外开窗的必要,城外之城的都市“景观”对城中之城的都市“景观”又意味着什么,而采光口、铝百叶空调出口和自然通风口的并存也暗示着中国建筑的实际状况并不鼓励一个密实一致的表皮。[11]
导致有效或无效的公共空间的社会权力秩序,以及这种秩序和更高层级的社会秩序的接口问题,在大多数评论中都令人遗憾地缺席了。[12] 事实上,就晨兴数学中心所在的中关村地区的既有文脉而言,从大的方面而言,我们有必要研究单位“大院”的社区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导致数学中心这座微型城市实际上是在一座特殊的小“城市”之中,其时熙熙攘攘,交通严重堵塞的中关村大街所意味着的真正的城市生活密度,因此与这座建筑无关;从小的方面而言,此类型的为“高级”知识分子而特别准备的 “象牙塔”式的建筑在科学院系统,乃至整个北方科研机构的固有的使用方式,也值得作历史和社会学的探究。个人空间一旦将它的尺度扩展到公共领域,哪怕只是几个房间的小机构,和外界仅有几个“针灸”式的小接点,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空间不是自为的,“内”“外”关系并不取决于静态的物理分隔,而更多地在于社会性的权力分配和动态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完成了使用者对于外部环境的感知,也确立和保障了他在空间秩序中的地位。
不难看到,张永和自己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这牵涉到我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他近年来做得较多的“城市的工作”,试图通过一个动态的方法来确立建筑单体和环境的关系,从而把建筑外表皮的问题解决,或说有点不可思议地“化解”在建筑内部。
关于建筑表皮和其内部的关系,在当代西方建筑师中存在两种典型的态度,其一是文丘里式的,即建筑表皮的与其内在空间之间是不同的逻辑,表皮强调形象和交流的功能可以脱离建筑内部而存在[13],库哈斯对于超大结构[mega-structure]的表皮与其内部不相关的看法也可以归入此类[14]。还有一种则是“表皮建筑” (借用大卫·勒斯巴热[David Leatherbarrow]的指代)的逻辑,这种逻辑也强调建筑表皮的交流性功能,但是与文丘里不同,这种交流是基于一种“无深度的表皮”,援用德勒兹的概念,在“BwO”即无器官的社会身体中,形象并不是我们习惯称之为表面性的东西,因为这个没有深度的表皮下面其实什么都没有了,其结果必然是一种是“浅建筑”,就是表皮代替结构成了建筑的主导因素,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彼此交错渗透,形成无数可能的交流层面,这种动态的交流层面不仅仅是建筑自身形态构成的依据,它将建筑设计的流通[circulation],空间配置,结构逻辑,视觉关系等传统考量一网打尽。
我们注意到,张永和以动态方法“化解”表皮问题的策略和这两者都不尽相同,很多时候,他始之于一种西方理论原型,终之于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理想的无社会情境的援用:
其一是用“同构”或“可大可小”的思想来搁置边界问题。有人批评张永和是“以建筑的方法来处理城市问题”,但是与罗西的“一座建筑就是一座城市”,或是富勒的基于生物体宏观和微观机构同构的“薄面”[thin surface]不同的是,张永和的“可大可小”不完全是基于建筑形态、社会组织或是生物机理层级之间的相似性,而是基于我们上面所讨论过的那种刘伶式的对于社会性身体的内向的分解能力。当建筑师在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大框架中并无真正的改变能力的时候,他可以拆解和编排的并不是宏观的权力运作的空间,而是身体的每一部分和多种形态之间的关系。
“在他的装置中,作为体验主体的人体,并不是抽象的人体或带有社会性的人体,而是具体的、个体的甚至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很多时候,人体是被‘分解’成局部的......对体验主体的分解同时也分解了空间。”[15]
严格地说来,被拆解出来的并不仅仅是“身体的局部或器官”,而是一个个“小我”,因为无论是“手、臂、指”(地上1.0~2.0m[16])“头”(“头宅”)或是眼(“窗宅”)都不是简单的官能,而是独立的有体验能力的主体,因此,对这样的空间的体验并不是托马斯·霍贝斯[Thomas Hobbes]的“有机身体”[organic body]的部件在Cyborg时代的高科技集成,它们更多的是“我观我”,即身体的“向内拆解”,一种私人身体内的尺度变换游戏。对于我讨论的题目而言,有意义的是这种“同构”或“可大可小”的思想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利用,得到了一个“全能”的可以把不同尺度变换为相应机能的身体。通过“我观我”,通过把内外的物理边界转化为私人身体内部的动态机能,表皮即身体和公共领域的边界问题,并没有被彻底解决,而是被暂时搁置了。
我认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中,中间尺度的街道/广场等等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而中国建筑传统中,讨论得最多的是宏观尺度的规划理论和微观结构的院落构成,缺席的恰恰是这个“街道”。在张永和的“城市针灸”和“院宅”理论之间,“城中之城”的建筑内部空间经营和作为真正的“城市工作”的总体规划之间,语焉不详的也恰恰是这个中间尺度。这种语焉不详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建筑师,而在于街道所承载的公共空间及其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城市中从来就没有高度发展过,自然也没有完备的研究和描述。“城市针灸”是把建筑单体和更大尺度的城市单元的接合部简化成了一个个没有空间特性的点,而内向性的“院宅”的最薄弱的地方恰恰是它着意回避的和外部城市的物理边界。[17]
其二是“可观”的理论使静态的内外关系转化为单向的“取景”或“成像”,张永和本人明确地反对“可画的建筑”,但他的被我概括为“可观”的理论,却暗合于当代西方理论中用“取景”[picturing]来代替“如画”[picturesque]的努力[18]。和晨兴数学中心的消极“景观”不同,他的柿子林别墅中的“拓扑景框”是一个动态的,把人在建筑中的运动本身作为成像过程的“取景”。这种“可观”的理念再一次指向传统中国建筑理论中的“借景”,其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对景”而在于“拓扑”,在建筑设计无力改变外部景观的情况下,通过在建筑单体内对观看的主体的拆解与重新组合,创造出了足不出户便可以对外在景观进行编排的可能,这正是中国古典园林里“因借”的要义。
对于我们讨论的主题,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一因借过程并没有真正消解身体的社会性边界,“可观”强调的是建筑内部对外部的单向观看而不是穿透身体表皮的双向交流,归根结底,由身体的向内拆解,这种观看是对外部世界在身体内部投影的摆布,是“我观我”。这一点在张永和的“影/室”中固然很清楚,在街戏这样诉诸于露天的都市经验的装置中则更意味深长,路人透过小孔看到的不仅仅是城市,更主要的是,是他们同时作为观者和被观者的表演,归根结底,是装置的发明者对于自己同时处于观看和被观看地位的想像。“我观我”的势在必然是因为在高密度的城市中,观看并不是自由的,而是有着产权、商业利益和政治因素的掣肘,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社会机制鼓励观者/被观者的双向交流,“借景”最终只能是无人喝彩的独自表演。
我认为张永和的水晶石公司总部一层改建是最彻底的贯彻了他“建筑单体向城市空间发展”的主张的一个例子,它的使用情况也因此变得更富有意味。原有建筑的板式立面被改造成了楔入街道空间的凹凸起伏的建筑表面,这似乎暗示着更多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接触面和交流机会,然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没有建立在撤除一切屏障基础上的公共可达性,没有街道经济所具有的商业动机,仅仅将会议室搬到临街并不能使得私人机构公共化,吸引路人对于建筑内部活动注意的也不见得是字面意义上的透明性[19],而是一种奇观性的效果——这种奇观的更可能和更直接的影响也许是,会议室中的人由于意识到了路人观看的可能,可能会形成一种下意识的表演心态,从而使得这种观看成了不自觉的自我审视(图5)。
其三,在张永和“可观”和“同构”的修辞中,间或掺杂着“自然”的神话,或者说,建筑单体之外的那个问题重重的公共领域无法忽略时,张永和有意识地用“自然”来置换了它,或是用“自然化”(“竹化”)的方法予以包裹和柔和。以竹海三城为例,这种策略具体体现在,在张永和定义的基本城市单元,即“院宅”或微型城市内,自然(竹林)成为缺席的公共生活的替代品,社会实践为内向的审美活动所替代,在这一切之外,自然(茫茫竹海)则成为未经描述的却是更现实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填充物或替代品,再一次,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对立由自然观照的主体和观照对象之间的古典性的关系所替代,矛盾似乎消失了,表皮也变得无关紧要,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审美契合已经在私人身体内部完成了(图6)。
这种思路在“两分宅”中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自然和宅院混融的模式。自然在这种模式中成了“可观”的客体,一方面身体的向外观望变成了两翼之间的内向自我审视,一方面通过用自然包裹、屏蔽和搁置身体之外的空间,有意模糊尺度间的差异和边界的物理宽度,达到“同构”的可能。但在实际的城市情境而不是在理想的野外基地中,这种概念上普适的,以柔和自然对生硬城市空间分野的调和并不是充分自由的。例如,在张永和的重庆西南生物工程基地的设计中,即便有大江恰好邻近,即便行人确实可以自由地使用他留出的“穿透”,由大街横穿建筑经公共坡道下降到江边,这种“穿透”和建筑空间和公众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必然关系,而“自然”也并没有和建筑发生必然的联系,原因就在于这三组平行的空间——街道/商业机构/自然——之间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性“穿透”,为物理和建筑性的“穿透”提供动机。[20]
值得说明的是,这篇有关表皮理论在中国接受的社会情境的文章之所以选择张永和,并不是因为张永和可以被看作“表皮建筑”在中国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也不是因为张永和的作品可以涵盖所有和表皮理论相关的社会情境,而是相对来说,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可能是近年来最具备理论自觉的中国建筑实践,围绕着他们的作品,有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建筑师如何介入公众领域的最直率的尝试,以及沟通中西建筑理论实践的最大努力。因此,以上的分析并不是针对某个建筑师个人的批评,而是对构成当代中国建筑创作的一般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检讨。
对于表皮问题的中国接受,固然有许多理论本身的逻辑可以探讨,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当今中国的复杂社会情境,虽然以一院一家同构千城万户的规划理念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那种真正具有结合公共空间和建筑内部的社会条件却远未形成——尤其是由于政治条件,人口压力和安全原因,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建筑”或公共建筑空间,这种空间强调的不仅仅是公共可达性,更主要的是大众参与社会生活的公共精神 [21],在这种情况下,张永和这样的“非常”中国建筑师面临的两难是,一方面普遍的个人主义倾向令他们由意识形态后退到对于“纯粹”的建筑语言的研究,并由于这种中立的态度成为中国建筑师圈内惟一坚持文化理想的群体,另一方面,在面对“宅院”之外的、他们所不熟悉的市井生活时,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又使得他们多少有些力不从心。由于中国建筑实践操作的“国情”,以张永和为代表的中国“非常建筑”的探索,对于建筑空间向城市公共生活的过渡并无太多干预的可能。诸如水晶石公司建筑表皮那样的实验,最终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建筑内部空间逻辑的外部注释,却不能通过真正的公共参与和内外交流,达到对建筑深度的向内消解和建筑单体的城市化。
本文无意于由这样一种现实而苛求于“非常”建筑师们的探索努力。由于建筑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出现充其量不过是一百年的事情,新的建筑类型和滞留的社会情境之间的巨大张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由于这种社会情境的改变比建筑革新要来得慢的多,中国式的“表皮建筑”一定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存在着更多的社会性问题,而中国建筑师也最没有理由无视这些社会性的问题。但是或许出于对意识形态的厌烦,中国建筑师对于建筑理论的解读却很少顾及社会现实,他们的“城市”“观看”“空间”通常都是无文化色彩,无上下文和“纯粹建筑”的,对于表皮理论的理解可能也很难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和不安的现实。正如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说的那样,当代艺术形式的危机或许就是它在将不可见的社会结构可见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过于消极的,有时甚至是自我欺骗的角色。如果本文能对这种情形起到一点小小的改变作用,那它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注释:
[1] 见Peter Collins, Changing ideas in Modern Architecture, Montreal & Kin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49-159. 这种生物学渊源虽然由来已久,但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身体”成为西方政治和消费文化的一个主导性议题,以及生物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virtual reality和cyborg等等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应用日趋成熟后,这种渊源才超越了隐喻的层面,成为可以操作的技术现实,参见注释2。
[2] 一般语义上的“表皮”或“皮肤”在英文建筑文献中的出现由来已久,(如Architecture Reader这样的入门书在谈到密斯对西格拉姆大厦的包裹时用skin指称它的玻璃幕墙),这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对于表皮理论的格外关注虽然关系极大,但却不宜混同,我在本文中的第一部分涉及的“表皮”侧重于由“表皮”和“皮肤”的一般语义所传达的当代西方建筑的社会情境,在第二部分中,我谈到的“表皮”侧重于近年来为西方建筑师所瞩目的表皮理论,严格说来那只是关于表皮的,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提出的有其边界的建筑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对于表皮在当代建筑学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寄寓了极大的热忱,例如Tzonis和LeFaivre称之为“皮肤热衷” [skin rigorism]的理论。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皮肤热衷”的出现有其历史和社会情境,这种理论主张和表皮的传统意涵的距离本身就已经隐含着这种情境的影响。参见注释1。
[3] 这里, “中国建筑传统”和对应的“身体” 相对于中性的,无上下文的“建筑”和“身体”是具体的指称,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区别地。
[4] 安妮之家是一个西方建筑中不多见的内倾性[Introspective] ——而不单纯是内向[inward]——的空间,这个空间没有室外,只有室内,对于外在世界的全部社会意义,他们不得不向内寻求。在长达三年的藏匿时间里,这种一家人同处斗室中严重的非正常状况(尤其对西方人而言)显然带来了问题。最新出版的安妮日记披露了处于青春期的安妮因此而来的苦恼,她“渴望着找一个男孩子接吻”,哪怕他就是彼得,那个她从前并不喜欢的一起藏匿的另一家的孩子,因为她别无选择。本质上,那个室外的丧失不仅仅是自由的丧失,而是文明人身体的社会功能的错乱与丧失。参见H. A. Enzer and S. Solotaroff-Enzer edited, Anne Frank: reflections on her life and legac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5] 《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
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6] “以天地为屋宇”“以屋宇为衣服”,以及“以衣裳为天地”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衣裳为[社会性的]皮肤”(“衣裳隐形以自障蔽”),这些似乎自相矛盾的命题所反映的不是观念的冲突,而是身体基于不同尺度的社会情境中不同权力主体的隐喻。关于衣服和皮肤的讨论,参见Zito Angela Silk and Skin: Significant Boundaries, A. Zito and T.E. Barlow,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文章可参见Robert Harris, "Clothes Make the Man: Dress, Modernity, Masculin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关于表皮和身体的“向内拆解”的关系,可参见Isabelle Duchesne, "The Body Under Body, the Face Behind the Face: Corporeal Disjunctions in Chinese Theater." 两者均见于1998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论文集,未公开印行。
[7] "interfacing"的提法见于Nikolaus Kuhnert 和 Angelika Schnell 对于fold的讨论,见 Arch plus, 1996 Apr., n.131, p.12~18,74~81, ISSN 0587~3452.
[8] 本文的社会学视角并不排斥“纯粹建筑”的思考方式,但是,针对特定的问题,特定学科的方法将有助于抓住那些关键的问题,例如Avrum Stroll认为,两类事物不具备表面的显著特性,光影、雷电这样非物体的事物,以云、树和人为各自代表的非固状物、线形物和活物。他的讨论显然有其特定的讨论边界,如果说亨利·莫尔的雕塑由体积的运动而展现其表面的重要,树木由于在尖端展开的分裂生长的方式导致了“表面”不如“网络”更能涵盖其生命活动的规律,像人这样的活物的“表面”的复杂性则首先是因为社会规范有时可以逆转个体行为的纯粹生物性。
[9] 张永和用苏州园林为例说明他的内向型建筑理念的中国渊源。
[10] 比如弗兰克·盖里。见方振宁与张永和的访谈。
[11] 正如勒斯巴热的讨论所暗示的那样,高能耗的工业建筑是现代表皮建筑的重要源头之一,依赖于人工通风的封闭式建筑施工和维护也是表皮的概念赖以生成的一个技术前提。建筑理念的贯彻在中国同样受到工业产业发展状况的掣肘。
[12] 很多时候,建筑的使用状况,比如像康明斯公司负责人重新颠倒“颠倒办公室”的做法,如果并不能被看作是判断建筑设计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至少是检验现实社会秩序中人们对建筑空间的理解的难得资料,值得注意和记录。
[13] 关于这种态度和“身体”的关系,萨拉·罗丝勒谈到男同性恋者对于装扮他们的皮肤的看法,并将其比附于建筑师对于建筑皮肤的理解。这篇文章总体的言下之意是,化妆,正如一切着装一样,都是一种人为的形象性的东西[image],和内里的血肉,骨骼,脏器等等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男同性恋者施以脂粉,着女儿装,是一种形象和实在之间的游戏,“看起来像什么”与“实际上是什么”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张力,或说让人不安和焦虑的东西。见Sarah Kroszler, "Drag Queen, Architects and the Skin," in The Fifth Column, v.10-n.2/3, 1998, pp.52~57.
[14] Rem Koolhaas, Conversation with Student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6.
[15] 张路峰,“非常体验”,《建筑师》非常建筑专辑,2004年四月号,总108期,44,45页.
[16] Zhang Yung-ho, "Time City p.s. Thin City ," in 32, v.1, p.11.
[17] 以唐代长安为例对中国规划史的讨论中,人们发现,街道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作为里坊分隔的 “大街”并不承载公共生活,它的非人尺度更多地只适用于小城市之间的军事性分隔。而里坊内部的大量“坊曲”很可能只是自发建设后形成的“零余空间”,专论参见XX《城市规划》。这种情形也反映在胡同的历史形成上并延续至今。
[18] James Corner, "Eidetic Operations and New Landscapes," 见James Corner ed.,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c1999.
[19] 其实在这种情形下,文丘里的“装饰性的遮蔽”[decorative sheds],比如一层不透明的巨幅广告遮盖,可能比透明隔断更坦率有效地构成公众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实际交流。
[20] 朱涛,“八步走向非常建筑”,《建筑师》非常建筑专辑,2004年四月号, 32~43页。
[21] 这里所使用的“建筑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所指的不仅仅是为公众所使用的空间,而是培育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精神”的空间,有广泛的公共资助和参与,由此北京中央公园被看作是中国近代公共空间建设的开始,而中国古代的那些公共使用的著名空间的公共性,例如唐代曲江,则仍有待讨论。 |
|
现有评论:0 [查看/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