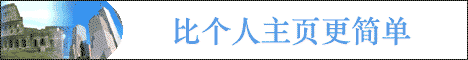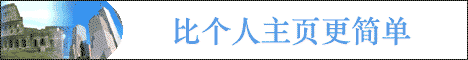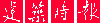
□ 本文发布于
2001-01-30 11:19:24
|
|
|
青涩少年与茫茫海岸
丁化
|
“海伦”,同事们时常提起这个名字,尤其是几个喜好艺术的。我知道海伦,是在《荷马史诗》的章节中,特洛亚战争因有这样一位美丽女神的出现而休止,“鸟儿停止了歌唱,河水倒流,花儿不再开放……”战士们忘记了厮杀,武器在人们内心地震般的惊撼里怦然落地——那是怎样惊心动魄的美丽,是怎样夺人眼目的光彩?荷马这个聪明的瞎子在对美的领悟和描述上,那睿智,那透彻,直让我们每个人都嫉妒。
海伦,是惊鸿一瞥的代名词。
所以当一纸“海伦画展”的信笺盈盈在手,便有一衣带水的向往和毫无道理的认同,只期待画如女神,把人震慑,让心眷顾。尽管太清楚不过,此“海伦”非彼“海伦”。
事实是,海是画,海伦是画者。
事实是,画是海,画者是海伦,杨海伦。
人是傍海而居又离海而去的游子;画是恬如婴孩又暴如君王的大海;画展则是游子与大海的休戚与共,大海与游子的爱恨别离。
感动在这里显得很虚弱,很苍白,一如用形容词堆砌的赞美对于绝色女子。
只是不晓得人淡如菊的国画怎会演绎出金戈铁马的声响,更不晓得浓墨重彩的油画又怎生出雨打芭蕉的写意。晓得的是,杨海伦的画,融会了上述两种技法的精髓,确乎“存于一心”而又“精骛八极”了。
《卷浪》是国画中的“犯冲”者,着墨与飞白的运用全然不似文人山水画般宁静祥和,刻意表现的浪头和看似无意的点染实则突出着作者横冲直撞的胸臆——水不仅是柔柔流动的旋律,更似纵横纠缠的交响。如此单纯的黑白,就这样构筑起一个复杂。这还不是极致,在《惊涛骇浪》中,这种构思的任情任性触目即是,不由夺人心魄,心生敬畏。
人在莫测的海的面前终究是无知的孩童,恭敬抑或失礼都不能改变海的傲慢。海是无情的君王,这大概是在海边长大的杨海伦所深深感受到的。每一轮潮汐送来的宝藏有多少,每一回风暴带走的生命就有多少---海,承载着一个二律背反;海,是一把双刃剑。
《童年的梦想》是画展里唯一眉目安祥的一张。有初升的朝霞染红礁石,有青涩的少年迎面远方。海是无边的神秘,海是不尽的畅想。
这神秘,这畅想,在《命运》里展现出的是海伦内心张力的扩充和思索的成熟。这一张的构图显然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亮红和墨黑交糅的远天,有浓绛和惨白混合的急浪。画面被近乎饱和的色泽所占据;可还有舟子一二,在天地之间。约略可见的是,楫断桨折前途惨淡,扣动心弦的是,逆流而上不曾湮沉,是真正的“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是真正的“谁会登临意”却把那“栏杆拍遍”。是失意的英雄,孤独的绝响;是盛年的佳人,肆意地开放;是不悔的囚徒,无望地攀援;是天火的盗纵者,泣血地含笑。
因表现的是海,所以画面驳杂丰富。船在画中的比例微乎其微;又因要表现的是人,只有人,才是天地的主宰,船,也就理所当然地在画面的中心,在观者的视觉兴奋点上。画者与画面的较量,到了观者这里,就是“我”与命运的较量。
我敢打赌,任你此刻是何样的心情,在驻足此画的片刻中,你读到自己。
你是莎翁,它就是哈姆雷特。来一千个莎翁,它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
画是另一面镜子,每个人都能照见容颜。这和画的是不是海,海里有没有人,都没有关系。不然该如何解释另一组《梦游》的看似抽象实际上是最天真的写实。在艺术面前,没有谁能真正成年。
最美的,永远是青涩的少年。
留连 穿梭在杨海伦的关于海,关于海与人的画的四周,海的具象是那么清晰,那么多彩。杨海伦对海的情愫是浓烈的。展厅里,不知从些什么位置上,音响里传送着海的声音。哦,海韵,具象了的海韵。音画交融,真有你的,杨海伦啊。我忽然醒悟了,这逼真的海浪声声,是真正的“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是明月在天,也是兵临城下;是似水年华,也是“流光容易把人杀”。海像所有让人爱恨交织的事物一样,给人永恒的抚慰和伤害,给人永恒的思念与挂牵。
和海浪声一样穿梭于画展之中的,是杨海伦。我默默地在一边注视着他,他那显得较大的头颅,那被海风无数次撕扯过的黑发间,有了几茎白发,那被海浪无数次地击打过的脸庞,含着几许微笑,显然不能惊艳特洛伊城的长老,相反,他的一支画笔,搅裹起观者心中的“战争”。
是《月光》的宁静,是《晨曦》的自由,是《惩罚》的无情。
是不同于史诗的惊骇,是迥异于自赏的婉约,更不是\"秀\"出来的成熟老到。
还是那青涩少年,还是那茫茫海岸。
|
|
纯粹建筑 | 理想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