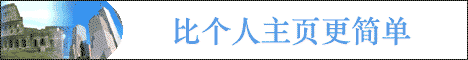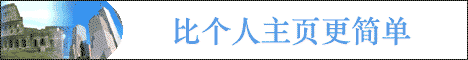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13-09-16 15:07:14
□ 阅读次数:13937
|
|
|
如何走向更好的城镇化
|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向以大拆大建为代表的盲目追求建设开发量的旧城市化模式告别。(摄影/朱骞)
如何走向更好的城镇化
访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
采访/佟鑫

诸大建: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联合国-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公共管理系主任。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观政策与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
新型城镇化这个话题吸引着关心中国城市发展的各方人士。从词源上看,新型城镇化和此前的新型城市化很容易混淆。新提法的重点是为了解决人如何在城市中长久居留的问题,需要集中多方智慧,更多着眼于制度设计层面,跳出城市规划的话语体系,从多学科研究的角度去分析,创造共同发声的环境。单纯追求提高城市化率,走粗放型的增长道路,或以抽象的提法替代实际的变革都不可取。本刊专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诸大建教授,谈如何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为中国城市的下一步发展选择合理的模式。
Q=城市中国 A=诸大建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Q:数据显示,在2012-2013年之交,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但这个数字与大量流动人口未能真正转化为城市居民的现实共同存在。您如何看待这种局面?
A:正确地理解新型城镇化,应明确其核心内涵是人的问题,人口进城并稳定下来成为市民,而不是简单的常住人口比重升高。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扣除16\%的流动人口,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过去30年,我们都把常住人口增长视为城市化率提高,现在发现这是泡沫,两亿多常住人口没有真正变成城市居民,没有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继续走旧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率达到60\%都没有意义。
区别于过去3 0 年的发展模式,在今后的10-20年当中,首先把两亿多常住人口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符合李克强总理谈到的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含义。国家发改委做过测算,认为一个农民进城变为市民需要10万元左右的投资,为解决其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需求,10万元乘以2亿人就等于20万亿的投资潜力。如果进一步加上增量农村人口进城,投资就需要更多。这是城市公共管理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型城市化与旧的城市化道路的一个区别。传统的形态研究相应要做的是如何在空间上合理安排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而不是继续大搞土地蔓延的开发建设。解决这个问题以后,50\%的城市化率就是真实的。再谋求增量发展,向2030年左右达到65-70\%的城市化率努力。
Q:从政府执政目标和学界观点来看,您认为新型城镇化作为城市发展目标应有怎样的内涵?
A:可以用一个球体来表示当前的城市化。球体分成三等分,下部表示土地空间和资源环境消耗,中部表示进城人口及相应的公共服务,上部表示制度安排,如图所示。首先,过去30年城市占用的土地空间和资源环境的消耗是超前的。目前全国耕地保有量已经逼近18亿亩红线。其次,人口进城及其得到的公共服务滞后于土地消耗和空间扩张。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的增长率与人口进城的增长率之比远远大于一,说明中国城市的土地消耗比人口增长要快得多,这种城市化是土地导向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导向的城市化。例如,上海的建设用地已经消耗2850平方公里,按照每平方公里接纳1万人的城市建设用地人口承载量估算,应该承载2850万人口,但是上海现在的常住人口是2300多万,超限使用的土地达500多平方公里。最后,制度安排以及配套政策严重滞后于人口增长和土地消耗。
从整个球体来看,有两个滞后局面。一是城市人口增长没有土地消耗快,二是人口要进城制度不匹配,体制抑制了人口进城。新型城镇化要解决这个不匹配问题。以2010年为基点,研究到2020年如何走出这个局面。我认为,好的城镇化就是三部分匹配,完整地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球体。
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创新

2013年2月26日,贵阳火车站迎来元宵节后返程客流又一高峰,处处是拖家带口的旅客进站上车。返乡农民工是主要的春运乘客,他们期待真正变成工作所在城市的居民。(图片/东方IC)

郑州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引下站队。子女教育是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应该享有的公共服务之一。(摄影/朱骞)
Q:如何实现人口增长与土地空间和资源消耗的匹配?与当前的城市发展模式相比,新型城镇化应带来哪些创新?
A:总的来说,新型城市化的方向,是减缓土地城市化的节奏,加快人口城市化的节奏。以上海为例,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要能够在285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不增加的情况下,促进人口增长与安居乐业,到2020年达到2850万人的城市规模,实现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相匹配。从全国情况来分析,需要强调从大到小、紧凑发展的四个战略:东部集聚、城市集群、生态包涵、垂直城市。
第一,东部集聚。雅安地震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处在著名的胡焕庸线上。胡焕庸线是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按照这个理论,不应该把更多城市布局在胡焕庸线以西。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在龙门山断裂带上有城市在继续发展,很多山区公路修建于汶川地震以后,这是违背发展规律的。资源环境条件告诉我们,中国不是全部国土都可以用来发展城市。麦肯锡2010年发布报告称,中国实现70\%的城市化率将有共计10亿人进城。这些人的大多数应该进入胡焕庸线以东的城市集中发展区域。
第二,城市集群。具体探讨胡焕庸线以东的城市应该以什么形式发展,从生态文明的观点看,我认为孤立的特大城市观点和孤立的中小城镇观点都不适合中国。经济学家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去研究,一般强调发展孤立的特大城市,认为人口越多越有利于集聚,对社会发展变量和资源环境变量考虑较少,比如提出上海应该做到3000万甚至更大的规模。环保学者强调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认为大城市模式有严重的城市病,不可持续,中小城镇才是首选。我的观点是中国不可能搞孤立的城市开发,简单地说中小城镇是新型城镇化的方向是不合适的。未来3-4亿增量人口,如果都进入中小城镇,其就业能力、公共服务、投资需求和环境压
力都将不可想象。最好的模式是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城市集群模式。中国需要建设7-10个城市集群,如果平均规模1亿人左右,就可以满足7-10亿人的城市化需求。过去30年,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城市群的发展,展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匹配的集群模式,符合十八大确定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原则。
第三,生态包涵。目前,生态城市的概念被泛化了,反而掩盖了真正应该强调的生态城市的空间关系。城市中三种空间的关系应该有如下规律:生态空间规模最大,社会空间规模居中,经济空间应该规模最小;同时生态空间包含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包含居住、休闲、交通等功能,经济空间包括工业园区、商业园区等方面。现在很多城市发展是以经济空间最大化同时侵占生态空间为特点的。很多以生态城市名义指导发展的城市,操作中都名不副实。城市的土地空间经济价值当然很大,如果把土地都变成水泥地,产业附加值当然很高,但城市就不是宜居的了。所以不能单纯从经济的层面去考量城市发展。
第四,垂直城市。城市规划有功能混合的概念,这不仅是一种形态上的概念,更应该强调是一种生活质量概念。因为功能混合的城市既节约土地空间,又能创造更高的生活质量。我一直认为,如果说世界是平的,那么就应该强调城市是尖的,需要通过功能混合、立体发展提高城市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例如,我们应该重视地铁、高铁等轨道交通站区上盖开发的战略意义。我们现有的城市,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城际轨道交通车站、高速铁路车站等,常常孤零零的远离居住中心和城
市中心。而日本的城市发展却形成了地铁、高铁等轨道交通为中心的城市综合体,其中包括就业、购物、休闲、酒店、换乘等功能,一个综合体可以服务二十多万人,也节约了土地。如果我们对每个站点的开发都应用这套思路,实现交通、居住、购物、就业四种功能一体化,城市的土地就可以有非常可观的节约效用。
Q:对已经进入城市但并未实现身份转变的常住人口,应采取哪些公共政策,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促进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A: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在半拉子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进城打工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过年都回到老家,循环往复,过着飞地式的生活。大量的农民工应该进入哪类城市?现实矛盾是:大城市公共服务好、就业机会多,但是户籍放开不容易。比如上海的教育、医疗、就业条件比较好,农民工喜欢,但是农民工子女进入上海的学校就读,一些上海人就发出了反对呼声。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购买公共服务的投资被稀释,享受不到以往那么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另一种选择是去中小城市。现在有人大力呼吁建设小城镇,但实际上农民工不太愿意去,小城市很容易落户,但就业机会少,社保条件一般,医疗和教育条件跟大城市相比差距太大。我认为存在第三条道路,就是在大城市旁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以大城市为依托,户籍容易解决,同时又可以得到大城市公共服务等的辐射,能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这应该是解决未来十年大城市人口过度密集问题的一个方向。对上海而言,市中心再怎么做大也无法承载这么多进城人口,就需要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溢出到嘉定、松江等周边二级城市,这些城市比小城镇和乡下的条件要好,制造业工作岗位多,购房和消费成本更低,这些城市也会因为农民的进入而逐渐发展起来。
Q:您认为在制度方面应该有哪些突破?
A:中国解放以后建立起来的人口血统论抑制了现在的农民进城,表现为三大制度障碍。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三是财税制度。这三个制度导致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三个最大的问题:一是城乡之间不平等,二是公私之间不平等,三是等级之间不平等。中国的户籍制度创设于1950年代,1958年真正确立,当时搞大跃进,城市没有能力支撑太多的人口进城,就搞了户籍制度,后来越来越严,变成一道屏障,把农民挡在城市外面。户籍制度的关键是其上附加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所以,废除户籍制度就是废除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这是伤筋动骨的改革,不太可能在全国一下子全面推开。可以做的也许是,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由小城镇到中等城市再到特大城市逐渐推进,第一步先放开小城镇的户籍,第二步在中等城市逐步放开,然后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根据居民居住的年限分批放开户籍.
现行土地制度也是1950年代确定的。解放后土地改革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到农民手里,有利于农民发挥积极性。但是此后过早地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搞合作社化和人民公社化,变成了公有制。改革开放之后才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致富和改变生存状态的第一桶金就是土地,可以用来解决就业、社保等问题,使晚年生活有所依靠,等等。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在一级市场垄断收购农民土地,低价收购、高价开发,即所谓土地财政,损害了农民应有的利益。要害问题是土地能否市场交易,使其财产性收入归农民所有。现行的土地制度抑制了土地要素流动,农民兄弟的财产得不到保值升值的机会,这是公私之间的不平等。土地制度创新,要成为农民创造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使其有能力在城市中解决居住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真正摆脱农民身份变成市民。现在有一些试点,包括嘉兴模式、成都模式、重庆模式、广州模式等。
城市当然有等级,但是中国的城市不是按照经济能力分等级,而是在按照行政资源分等级。从北上广等直辖城市依次往下到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获得的政府资源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条件好。这不是依靠市场的力量,而是按照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体现在财税制度上,就是新型城市化如何解决2亿常住人口的市民化投资。目前的制度性问题是中央有财权、地方有事权,基础公共服务由地方提供,但有关资金却由中央掌控。当各地仅仅按照户籍人口的规模规划、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就出现了常住人口得不到公共服务的空缺。实际上,与人口有关的政府服务和资金应该随人口一起转移,流动人口到哪里,相关的中央资金包括转移支付就应该到哪里。如果一个农民工在上海打工并且居住,他在老家的有关资金就应该转移到上海来,就可以解决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显然,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就无法为新型城市化创造制度条件。可以有两种改革政策的选择,一种方案是在中央控制财权的情况下收回事权,中央提供相关服务;另一种是在事权由地方负担的情况下,中央把财权交给地方。我个人认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事权是不一样的,基层更了解情况,中央很难了解,因此最好是事权、财权都归地方。这就是财政与制度相一致的城市化。
这三个制度决定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它们的变革都要触碰利益关系,这是新型城镇化需要攻坚的问题。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
Q:浙江的一些小城镇,容貌整洁、景观宜人、收入水平也较高,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您如何看待这些小城镇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
A:前面说过,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两种有代表性的模式。一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行政力量很容易推动,资源也都相对集中。大多数新城属于这样的模式,但是稍稍观察,就可以发现新城从农地上拔地而起,依赖产业项目,往往占地很大,但是缺乏人气,结果成为土地城市化的一种主要类型。例如,上海临港新城是在空无一人的土地上建设了10年,投资1000多亿,规划目标到2020年是80万人,但是现在的常住人口包括大学生在内也只有3、4万人。在中西部,很多新城的产业发展状态很差,房地产开发过猛,大量房屋空置,本地没有好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城市的失败几乎已经成为事实。
另一种是小城镇自下而上逐渐成长的发展模式,有市场推动的特点,它的难度在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没有重大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推动,难以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吸集更多的人气。改革开放后的所谓苏南模式就是这种类型。由于小城镇的人均占用土地高于大城市,往往没有规模经济效益,因此也容易导致另一种类型的土地城市化。
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模式中,浙江也许是发展比较好的事例。这些小城镇先是依托市场化的块状经济发展起来,然后与能级大的上位城市之间形成网络状的联系,成为一个大型城市区域的组成部分。因此,我的基本看法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应该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结合起来,在大城市一小时快速交通的范围内,把有一定人气的小城市做大,也许是比较合适的道路。这是包含以上两种模式有利因素的第三种道路。上海旁边的昆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事例
|
|
纯粹建筑 | 理想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