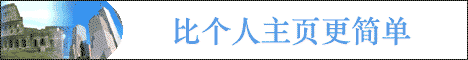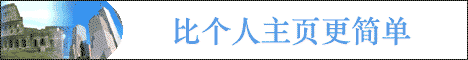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10-06-25 17:07:46
□ 阅读次数:14951
|
|
|
在原点上反躬自问
仲德崑
|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南京,210096)
在原点上反躬自问
——5.12汶川大地震引发的建筑思考
仲德崑
摘 要 通过对5.12汶川大地震的思考,作者提出对建筑基本原则问题上的反思,重新思考建筑的本质,并从建筑师职业操守的角度分析三种建筑师,提倡建筑师应主动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最后作者呼吁让建筑教育走出大学课堂,以提高全民族的建筑修养,创造产生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和优秀建筑作品的社会土壤。
关键词 建筑基本原则 职业操守 社会责任 建筑教育
中图分类号 TU-0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0-3959(2008)04-00-00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我当时正在北京做毕业设计调研。深夜,住在北新桥文化部招待所四楼的我,感到仿佛一个无形的大锤在击打整栋建筑,和其他恐怖的衣不遮体的人们一道逃离了建筑。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我正在成都西南交大进行建筑学专业评估,虽然地震时我们在室外,但仍感到站立不稳,在离开接近的建筑物时不得不手扶树木才到达安全地带。随后的日子里,看着电视上家园山崩地裂、城乡建筑倒塌、百姓生离死别的场面,特别是看到中小学校校舍、医院病房等人口最为密集的建筑物被“震碎”,无数稚嫩的生命还没有生长到成熟的阶段即瞬间消逝,青春的蓓蕾还没有等到绽放的一刻就惨遭摧残,我的心始终在颤抖,我的心灵始终在拷问自己。
有人说,这次汶川地震,13亿中国人都是难民。还有人说,汶川地震后,中国的一切都会有所改变。我以为有一定的道理。今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已经悄然实现了明显的进步。那么,汶川地震后的中国的建筑和建筑界会有什么反应?近几年积压在心中的块垒,是否也已到了应该一吐为快的时候了?
一 中国建筑设计现状的反思——方向的迷失
近年来,中国建筑界出现了一些有目共睹的现象。正如中国建筑学会近期在京召开的抗震救灾专家咨询会议指出的,“近年来的一些建筑设计过多地追求所谓的新奇特,只注重在建筑的造型和表皮上做文章,……”。[1]
可以理解,中国建筑学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表述十分克制。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大地上一些西方建筑师以及中国建筑师的作品所表现出的问题,已经显而易见地说明:当前我国建筑设计领域在根本法则问题上已经迷失了方向。仅仅列举两三个实例即可以看出,我们在建筑设计的基本方向上出了问题。
其一,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一座52层、高234 m,一座44层、高194 m,建筑面积47.3万m2,钢材用量近14万t(相当于3个“鸟巢”工程),造价超过百万人民币的扭曲的环状摩天大楼,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的“奇思妙想”,几乎全然无视建筑结构的基本原理,莫名其妙地将10层建筑主体悬挑70 m,造成在结构安全、消防疏散、空气调节等等方面的极不合理,甚至无法满足设计规范。我想,这种设计如果放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恐怕是不可能得以实施的。
其二,近几天媒体上炒得轰轰烈烈的成都市新行政中心拍卖变现用于灾区重建的事件,且不说其动机是否合理,仅就其设计来说,就很耐人寻思。在项目建设接近尾声时我曾经参观过现场。这个由安德鲁设计的名为“新益州城市广场”的行政中心建筑群,占地17 hm2,建筑面积约37万m2,总投资约12亿元,被网友称为“不仅质量过硬在地震中毫发无损,而且前卫、大气、考究得堪与北京的奥运工程‘鸟巢’媲美”。新行政办公中心的构思理念是“芙蓉花开”,由中心是椭圆形的会议中心建筑——“花蕊”,6幢花瓣形高层阶梯建筑环绕一圈呈放射状布局。每一个“花瓣”建筑的中心是一个中庭,外围护结构是玻璃幕墙,外面覆盖有一层仅起装饰作用的钢质结构格网。6朵花瓣形建筑中至少有3栋以东西向为主。不言而喻,除了设计理念上的问题之外,其节能减排方面也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其三,由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子公司AREP公司设计的上海铁路南站,建筑面积近8万m2,日旅客接待能力可超4万人次。一个形似飞碟,直径达255 m的圆形建筑,18根放射形主梁使它看起来像冉冉升起的太阳。据设计者让·马里·迪蒂耶尔说,上海位于中国东部,且经济发展迅速,太阳型火车站将很好地代表该城市的形象。站内候车厅与服务设施层形成一个像圆形剧场一样的开放空间,整个车站的功能及通向服务设施的路线因此一目了然①。
然而,这栋建筑对于形式的追求,恰恰使得它作为交通建筑的根本属性——流线的便捷和明晰的方位感——出了问题。据《南方周末》的抽样调查,65%的人有过在南站迷路的经历。让人实在不明白的是,这种对于方向感要求强烈的建筑类型,为什么要采用方向感极差的圆形。难道只是要实现设计者喜好的象征东方的“太阳”构思吗?该文作者质疑,“数不清的出口、标志、通道摆在你面前,如进迷宫。对偌大一个‘高进低出、南北贯通’的圆,旅客群体智商不够用!上海南站标志性的‘景观’是:询问声不绝于耳,工作人员、志愿者不厌其烦的嘶哑的回答声……尤其节假日学生潮、民工潮,场面更壮观:人们拖着大包小包,祖国各地的口音搀杂在一起,其实只问三个字:怎么走?”作者最后甚至问:我们能否起诉建筑设计者②?
我以为,可以将这种困境归结为人们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所产生的信念危机,在由自然科学主导的学科范式的强大压力下,传统理论已经无人问津,而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后果,又使得功能主义原则作为设计法则备受质疑。思想上的混乱,使得今天的建筑师几乎可以无视“适用”与否,“经济”与否,也可以不考虑“美观”与否,只要“新”、“奇”、“特”。
其实,对于这种现象的抨击,并非自今日始。吴良镛先生在其执笔的《北京宪章》中呼吁“回归基本原理”(back to the basic concerns)[2]。许多有识之士在多种场合均有过精辟的论述,直至6.3中国建筑学会专家咨询会联名呼吁重提“适用、经济、美观的建筑方针三要素”,并“加入安全这一重要因素”[1]。
对当前的建筑界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再次给建筑师提供一种明确的方向感。”[3]我以为,此时此地,我们应该进行一次原点上的反躬自问:建筑究竟是什么?建筑的根本法则是什么?
二 建筑的根本法则——让我们在原点上反躬自问
事实上,在建筑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已经从自然和建筑的自身规律中提取出一些可供依循的基本原则或者法则,并一直被作为建筑实践的方向。
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建筑必须满足三个要求:坚固、实用、美观。关于建筑学的学科地位,维特鲁威断言,建筑是最早出现的艺术与科学,因而是所有艺术中居于第一位的艺术。
文艺复兴时期的阿尔伯蒂是一个基于诠释之上的开拓者。他既不是一个中世纪意义上的工匠,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建筑师,而是一个贵族化了的业余爱好者,一个建筑的“发烧友”。在其十册巨著《建筑论》中,他从建筑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来进行论证——“它会在所有方面带给人类以最大的便捷,这既包括公共领域,也包括私人领域;它的高贵绝不亚于世上任何最为杰出的事物。”阿尔伯蒂将建筑师所起的作用清晰地定义为人类环境的一个富于责任感的塑造者[4]。
阿尔伯蒂在《建筑论》中所提出的类型学和个性说一方面解决了法则的约束性问题,一方面解决了法则的创造性问题。约束的依据在于特定的功能,创造的依据在于特定功能的特定性格。藉此,建筑的整齐与变化,法则和个性,内在功能和外在形式等方面,获得了空前的张力[5]。
19世纪的德国建筑学家克伦策(Leo Von Klenze)给建筑下出了这样的定义:“从词语的真实意义——伦理的意义上说,建筑是基于人类社会及其需求目的之上的、对自然材料铸造和结合的艺术。”[6]
莫里斯(Morris)更加关心建筑的社会意义,他将建筑师的责任延伸至设计的每个层面,将建筑视为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在他看来,建筑设计上的“简单”,具有伦理的价值,因为这与大众的需求紧密联系,同时不恰当地机械使用旧有的风格是社会道德风尚进步的障碍。类似于莫里斯,柯布西耶也关注建筑师的社会责任,他高度赞扬理性主义和标准化的机械生产,试图以此来打破旧有的追求形式和风格的创作态度,并寻求以建筑的手段创立新的社会秩序。
吉迪翁在阐述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意义时指出:“现代建筑学是以道德问题作为其出发点的……它为当代的生活提供了了一个新的背景,这个新的背景又会反作用于它得以产生的社会生活。这种新的背景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观念产生改变和发展。”[7]
现代建筑先驱法国建筑家奥莱特-勒-迪克(Viollet-le-Duc)认为,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用理性来加以解释,或曰都可以简约为理性的表达方式。他拒绝风格对建筑的控制,“风格仅仅是理性能力在一个目标或客体上的具体的运用或体现”[8]。
1911年工艺美术运动干将莱特比(William Richard Lethaby)在他的著作《建筑学:建筑艺术理论和历史导论》(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Building)中提出:“一个高尚的建筑并不是某个天才设计师的设计行为的产品,它是对时代经验总结的结果……一个真正的和真实的建筑不是意志、设计或学术的产物,而是对建筑之中本质事物的揭露和发现,像语言、作品和对金属的使用一样。”[8]
密斯在1923年写到:“在建筑之中我们拒绝了所有的审美的猜想,所有的教条和所有的程式。建筑就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空间形式表达;是对生活、变化和新事物的表达。”[9]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建造技术适应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战争以及战后重建对住房的大规模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运动先驱们所探寻的“时代精神”逐渐与技术理性主义相结合,成为现代主义者奉为教条的法则。
20世纪20年代,柯布西耶在设计郊区住宅时,就已经建立在帕拉第奥的数控先例之上(后来科林·罗向战后的现代主义者揭示了这一点),到50年代,柯布西耶设计的所有建筑都是基于模数基础之上的——一种取自古代黄金分割的理性比例体系。用类似的方法,密斯在战后也发生了转变,他抛弃了早期动感的、离心的构图,转而喜爱帕拉第奥式集中的、静态的秩序,这在柏林国家美术馆中达到了顶峰。这种模数的概念通过控制线和几何规则将空间、时间和文化的差异统一化,将人体的物理需求以数字的方式定量反映,并由此创造出一种机械主义的美学效果。
与这种几何化、模数化的建筑秩序相对应的是工业化的规模生产。面对战争遗留下来的诸多社会实际问题,柯布西耶天才地将现代科学与社会理想融合在一起。1914年,“多米诺”被提出。这种体系完全独立于平面功能,只承载楼板和楼梯,由标准化构件组成,由此可以应对不同的组合需要。钢筋混凝土的结构适应了现场施工的需要,所有部件都可以由专门的工厂批量化大规模生产。由于承重结构的独立,它的内外墙可以使用任何材料,“特别是那些下下选之料,诸如历经火海的石灰石,用战后的瓦砾残渣制成的煤砖等等”。通过这种造价低廉、可以快速复制和随意组合的体系,柯布西耶设想普通的民众可以自己动手建造自己的家园:“一言以蔽之,我们所设想的是灾民源于他们的主动性漂漂亮亮地建起6个、12个或者18个基础的方墩,向承包公司预定1个、2个或者3个多米诺骨架。另外,向兄弟公司预定住宅配套设施所需的各种物品。然后,一笔资金加上自己的力气,灾民的新家就在他们自己的手上建立起来了。没有任何技术上的担忧,不需要任何专家,每一个人都可以盖自己的房子,遂自己的心愿。”通过这种全新的全民建造方式,柯布西耶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美好的生活画面:“它会给人以安静、规矩、干净利落的印象,并必然会将纪律植入居民心中。”抱着相同的理想,格罗皮乌斯在德国南部乌尔姆(Ulm)造型艺术学院任教时,鼓励学生们开发适合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设计;密斯则提出了“万能空间”的概念,他通过对混凝土、玻璃和钢材的组合使用将工业化建造推向了一种无个性、大批量的、组装化的国际主义风格。
和国际式产生的背景类似,经历了一个世纪战乱的中国,于1950年代提出了建筑三原则: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这是针对中国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所作的正确选择。后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建筑界已“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做了必要的修正。我以为“适用,经济,美观”这一普适的原则,对于今天的中国,特别是在大量性、功能性的建筑的设计中,如学校、医院和住宅等建筑类型,仍然是不能忽视的基本原则。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建筑产生于人类对于遮风蔽雨的需求。但它很快就成了技术技能以及精神和社会目标的基本表现。建筑的历史是对人类的创造力的总结,对和谐和价值观的感受;它是个人和社会的复杂意向的完美反映。现代建筑的先驱们寻求工业技术和新的形式,因为它们提供了创造的自由和社会改善的机会。而如今这些技术的巨大潜力只被用于一个目的——赚钱。产生建筑的人类意向的丰富复杂性今天已经被剥得赤裸裸的了。借用一位和我同时考察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作品的荷兰建筑师的感慨:今天,我们已经不懂得建筑是什么了。
三 建筑是什么——社会赋予的任务已使得建筑不堪重任
1949年,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西方列强的欺凌之后,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尤其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以后,终于“有钱了”,总希望能扬眉吐气,以体现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欣喜之情。然而,不幸的是,在城市化高速发展、建筑业如火如荼的今日中国,社会选中了建筑作为这种心态的载体。建筑被寄予过高的社会期望,人们不约而同地指望它们成为当代中国人的骄傲、自信、梦想和创造力的象征符号。“建筑、尤其是体量巨大的标志性建筑的力量在于,无论它曾引发过多少争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最为雄辩的答复。除非时间证明,它的确是丑陋、骄傲、奢靡和不正当的,否则它将始终呈现在文化图景中,记录着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节点,记录着人们的梦想,它有时会超越功能性评价和道德评价,而成为凝结在大地上的诗篇。而这样的建筑物,正是经济持续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中国所期盼的,也是文化自豪感日渐苏醒的中国人所召唤的。所以,当鸟巢在北京的北四环逐渐亮相的时候,人们或多或少都会为此感到骄傲,因为人们相信,或许只有在当代中国,这种具备‘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和无与伦比的震撼力’的建筑才能够成为现实。”③
那么,建筑究竟是什么?前文说过,建筑产生于人类对于遮风蔽雨的需求。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赋予建筑过多本质之外的重任,已使得建筑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或者套用一句常用的说法——走进了误区。
在我们的一些城市领导者、政府官员的眼中,建筑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工具。我遇到过的不少地方首脑都要把他治下的城市“做大、做强”;前一任规划向东发展,他势必向西挺进;上任伊始,必提出“三年一大变,一年一小变”的口号;只要启动一重要项目设计,必要求建筑师做到“30年不落后”甚或“50年不落后”;建筑设计项目招投标,必邀请境外建筑师操刀,甚至提出不得邀请国内设计单位参加(因为这也体现他们的“政绩)。规划设计方案经专家评审后,必定要由地方或单位最高行政长官确定实施方案(不知如若医生嘱咐他去做CT,他是否敢去做B超)。
对于一些开发商来说,建筑追求的几乎仅仅是利润。与市场上经济性的商品、公司的帐目平衡表上数字相比,新的建筑物的意义高不了多少。对利润的追求决定它们的形式、质量和表现。设计中任何不与产生短期利润直接相关的开销,常常不被接受。正如英国务实的经济学 —— 撒切尔主义企业家洛德·汉森(Lord Hanson)令人震惊地把开发商的目的描述为“今天挣明天的钱”——对只能经过长时期才能得到回报的生态技术方面的投资丝毫不感兴趣。这一战略,只能使明天变得更糟,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思维背道而驰。
他们几乎完全无视对于好的建筑来说是十分根本的美学要素:比如,建造作为公共场所的灰空间,比如柱廊,廊道等无法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常常被认为全无必要。对于公共空间的营造、环境的绿化美化,如果与房地产的销售和经济效益无关,也是被压缩到最少。
仔细地考察一个一般的商业建筑,你会看到它是如何的贫乏和粗野。经过一个世纪的完善,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从未能够像今天这样造价低廉,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建造得如此低级。或是“欧陆式”的,或是仿佛是从商品目录中选出来的现代立面,与地方和人文毫不相干。各种类型的建筑都被加以包装,并且标准化了;对建筑师的选择往往依据他们收费的低廉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质量。
建筑行业已经堕落到用最少的金钱和最短的时间,生产出最大的容积,并用这一种或另一种安装上去的样式包装它们的立面的地步[10]。
对于有些建筑师来说,比如库哈斯之流,建筑只是反映他们的个人意志、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筹码。
法国建筑师兼记者特莱蒂亚克(P. Tretiack)所著的《应当绞死建筑师吗?》中的库哈斯其人,既是一位激进的极端分子,一位“彻底的幻视者”(visionnaire total),又是一位善于经营、极其精明的商人。库哈斯来自荷兰的鹿特丹这个二战中被炸为平地的城市,战后完全是在一张白纸上重建起来,这与库哈斯的“彻底砸碎”、“从零开始”(To start from scratch)或“操你妈,文脉!”(Fuck the context)有直接关系。所以库哈斯设计的方案多是“惊世骇俗”、甚至反自然的。
书中说,库哈斯的过人之处,是他能言善辨。他的得奖或“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设计,不如说是因为他的“理论”。他有一套非常能蒙人、能把死的说活的辩术。他像一位巫师,在一阵阵让人目瞪口呆、似懂非懂、飘浮在无限美妙幻景的“咒语”作用下,到处得手:“他诱惑了各种行政官员,…… 欺骗(dupe)、操纵(manipulate)他的对话者,让他们很高兴终于找到一位自有一套关于城市理论的建筑师。”比如他的央视方案,端出一个美妙无比的“巨环”说:“我们将把电视制作的所有部门都囊括在一个连续的巨环中,使它可以自我运转不息”(《南方周末》2003.4.3)。论证图片中还有一条红线,环形流转。哪个内心纯朴的官员和“专家”会不被这样美妙的“论证”所“诱惑”而折服?而这样的循环事实上并不存在[11]。
整个一江湖术士!一个玩世不恭者!他说,“这就是中国现在需要的建筑,我给你们带来了!”后来,果然库哈斯的方案成为终选。善良的专家们的评语说:“专家评委认为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鲜明个性,又无排他性。作为一个优美、有力的雕塑形象,它既能代表北京的新形象,又可以用建筑语言表达电视媒体的重要性和文化性。其结构方案新颖、可实施……”库哈斯可以得意地说,“是你们自己选择了它……”,正像北京土话说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前述三类人,是社会的建筑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对待建筑的态度,是当今建筑设计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他们代表社会赋予建筑的任务已使得建筑不堪重任,因而使得建筑被异化。
四 三种建筑师——建筑师的职业操守
为谁设计,为什么设计,如何设计,是每一个建筑师毕身都得回答的问题。正常的回答,或许可以校正我们前进的脚步。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到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可能已经被人们所淡忘。如今,已没人再提到这个问题,甚至认为这已经不是个问题。其实,作为建筑师,我们时时在用我们的实践回答这个问题。
如今,有三种建筑师。第一种,人们称之为“明星建筑师”。这些建筑师倾向于把建筑视为个人意志的表达。他们往往十分强调建筑的表现功能,他们往往和媒体共同合作(通常是非建筑专业媒体),推出自己的作品和理念。就像时装设计师中的大师,他们的作品就好似“T形台”上的时装,虽然不太能直接穿上大街,可是,他们引领潮流。我以为,社会需要“明星建筑师”,而且,当今中国的一批“明星建筑师”,总体表现不错。但是,“明星建筑师”不能太多。盖里设计的建筑,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至多两个。如果满大街都是这种建筑,睡觉时会做恶梦的!当然,也不会太多,一个成熟的社会毕竟会是理性的。
第二种建筑师,我称之为“商业建筑师”。这些建筑师唯业主马首是瞻,只要能收到设计费,你要方的,给你方的;你要圆的,给你圆的。“欧陆式”、“Townhouse”、“英伦小镇”、“花园洋房”、“白宫”、“天安门、金水桥”,信手拈来。容积率、覆盖率、绿地率总可以瞒天过海,满足要求。对于他们,是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可言的。
所幸的是,在当今中国,第三种建筑师“主流建筑师”是绝大多数。他们认为,一个好的建筑应该是反映当代人类文化成果、创造明日更好生活环境的建筑。它是科学技术、哲学及艺术的综合结晶。它满足社会需求,尊重自然,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他们强调建筑师的社会责任,他们坚信建筑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
如果说汶川大地震以后,中国的建筑和建筑界会有什么变化的话,我想,应该是第三种建筑师会越来越多,为我们的社会提供更多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建筑,同时对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应该探讨一种途径,使建筑能够根据其使用者变化的需求来丰富我们城市的公共空间,并且寻找可持续发展并防止污染的技术。建筑物应该激发,并且构成满足社会需求和尊重自然的城市。我们当今对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的需求提供了重振雄风和形成新的美学秩序的机遇——它可能成为建筑学专业复兴的原动力[10]。
五 让建筑教育走出大学课堂——提高全民族的建筑修养
探究中国建筑的困境的根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全民族建筑文化素养的低下。试想,一个社会的决策者、投资者们不懂得建筑文化,不了解建筑的基本法则,如何产生优秀的建筑产品?
据我所知,在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中学就开设建筑艺术课程或建筑历史课程,美国的大学常常利用暑假开设中学生夏季班,相当于我国的夏令营,向中学生传授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扩大建筑学的生源。欧美国家的电视、广播等媒体也常有像“十字路口的建筑(BBC)”这样高水平的科普节目,以提高大众的建筑素养。近期,中央电视台作了一台题为“为中国而设计”系列片,希望这个专题节目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不是误导大众(但愿我不是杞人忧天!)。
只有当全民族的建筑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政府官员和管理者、开发商和投资商对建筑优劣的判断有了一定的品味,知道什么是合理的规划,什么是优秀的设计,什么是好的建筑;也明白什么是像央视新大楼一样的荒唐建筑,什么是像“福禄寿三星”宾馆、沈阳某“铜钱银行”(一位台湾李姓“大师”的设计)那样的恶俗文化,什么是像汶川地震中夺取无数中小学生性命的伪劣产品;特别是应该知道应该把设计交给什么样的建筑师去做,不是那些如库哈斯之流不负责任的洋建筑师,而是大多数本土的优秀的“主流建筑师”和“明星建筑师”以及像理查德·罗杰斯这样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洋建筑师,才是值得信赖的建筑师。
只有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素养和建筑规划知识得到根本的提高,我们才能期待在我们的国土上出现世界级的建筑大师,世界级的优秀建筑作品。我们把这个希望寄托于当今活跃在建筑舞台上的中青年建筑师和即将步入建筑设计行业的莘莘学子身上。
作为一个建筑教育者,我呼吁让建筑教育走出大学讲堂,把那些普通的建筑素质教育部分,向大学的其他学科院系、向社会、向中学延伸,使其成为社会人群的素质教育内容,类似普通的美术、音乐教育。建筑师和大学教授应主动承担教育全社会、教育业主和教育普通市民的责任,写科普书籍,走上电视和广播媒体,向全社会普及建筑基本原理和法则,普及建筑文化和建筑历史知识,普及建筑安全和防震常识,以提高全社会,包括业主、政府官员的建筑欣赏能力和批评能力。唯有如此,中国的建筑才会有灿烂的明天。
注释
① 参见: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060627/n243971577.shtml.
②参见:李水苍,《南方周末》:上海南站让人找不到北,http://shbbs.soufun.com/1210108940~-1~3627/43176303_43176303.htm.
③参见:蔡方华,“十大建筑”青睐中国?欣喜之余更应省思,新浪论坛,http://bbs.uc.sina.com.cn/tableforum/App/view.php?bbsid=244&tbid=4519&fid=11677.
参考文献
[1] 本刊编辑部. 中国建筑学会在京召开抗震救灾专家咨询会议. 建筑学报,2008(6):2-3.
[2] 吴良镛. 北京宪章.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3] 哈里斯K. 绪论:后现代的前奏. 建筑的伦理功能. 申嘉,陈朝晖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4] 阿尔伯蒂. 建筑论,VI.I. James Leoni,英译本. 伦敦:[出版社不详],1955.
[5] 杨健. 论西方建筑理论中关于法则问题的研究方法. 重庆:重庆大学博士论文,2008.
[6] 克鲁夫特HW. 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 王贵祥译.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
[7] Giedion S. Space,Time and Architecture,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8] Watkin D. Morality and Architecture. London:OXFORD,1977.
[9] Johnson PC. Mies van der Rohe. New York:Museum of Modern Art,1953.
[10] 罗杰斯 R. 小小地球上的城市. 仲德崑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11] Tretiack P. Faut-il pendre les architectes? Paris:Seuil,2001.
收搞日期 2008-07-15
|
|
纯粹建筑 | 理想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