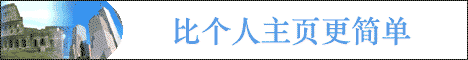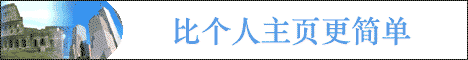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07-05-27 11:40:51
□ 阅读次数:75449
|
|
|
软建筑
虞刚
|
【摘要】荷兰建筑师拉斯·斯普布洛伊克(Lars Spuybreok)一直在进行着富于创新性的实验性设计。他试图通过对相关学科的研究和试验建立某种新的设计模式和方法,并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以建筑师"经验"为主导的设计方法。对他的设计作品的讨论,一方面将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建筑设计和教育中某些既定的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将有利于我们对计算机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产生更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设计研究 数字设计 设计程序 软建筑
Abstract: A leading Dutch theorist and architect, Lars Spuybroek (principal of NOX) pushes architecture in incredibly improbable, winding, curving, globular directions. Influenced by neurology and philosophy, and ever-more intricate computer modeling, he researches whether building movement can more comfortably reflect body movement. In his design the operative idea is no longer that form follows function, etc; it's a unified system, from system to flexibility to rigidity to morphology. His projects thus lead to "soft" architectural biomorph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help us reconsider the existed concepts in the architecture, and to benefit to us understand digital architecture.
Key Words: design as research, digital design, design procedure, soft architecture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一组组单个的动因在寻求相互适应与自我延续中或这样、或那样地超越了自己,从而获得了生命、思想、目的这些作为单个的动因永远不可能具有的集成的特征。
——《复杂》
一般来说,当代建筑学对曲线型不规则建筑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倾向:第一种是对相对静止的曲线型不规则建筑形态的研究,一种静态物质的混乱状态研究,照字面意思即一种对物质空间的物理现象模式研究,比如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第二种关注的是一种建筑处理过程中的流动性和平滑性,以至于可以通过不同系统的流动或循环以及内部空间的安排来间接体验到形态的柔性,比如格雷格·林(Greg Lynn)的胚芽住宅设计研究以及其他作品。
比较而言,第一种倾向也许会把精力完全放在对最终形态的研究上,醉心于某种艺术形态的创想(这必须依靠某种艺术天赋或与生俱来的艺术敏锐性),或许同时也要忽视或有意扭曲建筑设计过程。第二种倾向中的建筑也许会以非常中性和普遍化的状态来实现,也就是说,也许会走到现代主义关注抽象空间而不关注身体或人自身感受的老路上。[1]
在这样的一种思考下,荷兰建筑师拉斯·斯普布洛伊克(Lars Spuybreok)希望提出一种不同于两者的模式,一种“建筑软化”的模式。[2] 这种模式也许会避开这两种倾向:由于斯普布洛伊克认为建筑是易变的同时又会对其中的使用者作出相应反应,因而,建筑完全可以被解读为“形态(身体)+程序(日常生活)”[3](form[body]+program[routine]),而这正是“软建筑”的定义。按彼得·塞纳(Peter Zellner)说法[4],“软建筑”将把建筑的弹性与身体的弹性连为一体。斯普布洛伊克认为:
……(上述)两个倾向在当代文化中一直在不断加强,但是,肯定存在(其他)可能性。工具主义者(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在调和身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矛盾,并必将影响或改变身体及其周围世界。实际上,有两种途径来反对这种技术决定论说法。第一种:建筑目标和技术目标的完全融合。第二种:身体与技术的完全融合。在第一种途径中,建筑特征消失了(这并不是坏事)。在第二种途径中,身体的灵魂已经毫不费力的逐渐向生物工程技术转变(这也不是坏事)。在这两种途径中,技术希望实现人体的镇定,调节人体并保持人体平静,以便为人体提供一种经过协调的气氛,比如在提高了几层楼高度的时候仍保持人体的静止,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促进人体入睡。但是,也许很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形:比如技术向推进人体加速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保持人体镇定;或者建筑完全被技术吞没,以至于建筑完全可以减缓或者增强人体的节律。[5]
从这段话我们会发现,不管出现什么情形,斯普布洛伊克都希望把身体、建筑和技术融合起来产生一种混凝土式的血与肉,也就是说创造一种这三者之间的新型的积极互动关系。简而言之,软建筑是一种人、建筑和技术会在其中产生交互作用的建筑。在所谓的“软建筑”中,身体不会被迫与技术同步,建筑也不会完全替代身体的所有行为。比如在一般的建筑中,当设置不同的门时,比如推拉门、平开门或旋转门,人的身体会被迫随着门技术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反应。但是,在软建筑中,我们的身体会对周围环境作出相应的积极反应或者互动,而不会因为技术而产生惰性。斯普布洛伊克写道:
现在,我们仅仅知道这三者之间以比较平衡的关系共存。但是实际上,在这种共存关系中,技术似乎抑制不住地试图力争取代人类身体的所有行为(比如计算机对各种人类感觉的模拟)……但是,如果当我们生活中的各种装置替代身体运行发展到身体行为完全瘫痪的程度时,身体反而会利用自身的运动神经系统和韧性,尽力恢复每一种行为的运作,以便外部影响降至最低。[6]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来设想另一种建筑——这种建筑将拥有改变身体运行周期和循环周期的能力。这种建筑不是想获得一种舒适的效果,也就是说不会让身体变得越来越懒,而会增强人类身体的塑性和韧性,以便把身体与一种先进的技术环境整合为一体。这样,建筑就与身体的可动性、速度和运动产生直接关系,并进而促进身体灵活性的不断发展。这便是“软建筑”及其设想的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软建筑”策略会与“让建筑动起来”的策略产生局部的交叉,但是相比之下,“软建筑”更多的会考虑到建筑与人类身体之间的互动,而“让建筑动起来”则更为强调建筑本身的物理运动。
斯普布洛伊克在这方面提供了研究形设计实践的极佳示范,他试图将建筑与其他媒体、各种同步装置、视频影像、文字、房屋甚至杂志相互杂交来实现这种效果。他综合了生物学、(脑)神经学、考古学、绘画、电影软件特效和数字基因工程方面的启示和发现而创造出各种弯曲的建筑形态,并让这些形态处于某种生物体与数字技术之间的过渡区域之中。斯普布洛伊克认为:“我们正在体验一种语言世界、性别世界以及肉体世界的极端液态化……(我们已经进入)一种状态,一种所有事物都变得媒介化的状态,一种所有物体和空间都与他们在媒体中的表象相互融合的状态,一种所有形态都与信息相互混合的状态。”[7]
对身体、空间和视像的研究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斯普布洛伊克首先考察了空间与身体的关系,看看身体是如何对空间作出反应的。这里,他将引入一个神经学术语——“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通过这个神经学术语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身体和空间的关系。斯普布洛伊克认为,如果要解释像本体感受这样的术语,像奥立佛·萨克斯 (Oliver Sacks)[8] 这样的专业神经学家会给我们提供切实的帮助。他所写的最著名的书《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编撰了20个案例研究,这些案例都来自他在纽约工作时所面对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当代神经学家也许是世界上最反对笛卡儿的思想家。他们都对心理学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不相信存在漂浮在肉体之上的“自我”。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存在“心身分离”,他们相信只存在一种不断反馈循环的、结构上不断变化不断互动的复杂系统。对这些思想家来说,意识并不是投射世界的圣殿,也不是人们观察世界的源泉。这些神经学家将让建筑师们意识到,意识只是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一部分,只是身体自身及身体变形的一部分。[9]
对斯普布洛伊克而言,“本体感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为他提供很多的启发。本体感受是身体的自我知觉,但却是看不见的、无意识的。本体感受是人运动时所产生的一种内部肌肉意识和肌腱意识。本体感受完全是自发的。实际上,当一个人丧失他的本体感受时(萨克斯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他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借助纯粹的意识注意力来弥补这种缺陷。比如,如果本体感受丧失了,那个人将无法拿起桌上的杯子送到嘴边喝咖啡,他必须借助眼睛在意识上同步锁定杯子,并将杯子“送到”嘴边,眼睛决不能有半刻离开杯子。[10] 因此,本体感受是惟一与姿势相关的一种运动感觉。建筑师通常都认为,空间外在于身体,同时,空间为运动提供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实际上,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运动却是身体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更有意思的是,身体结构是塑性的,是可以变形的。例如,如果一个人的腿骨折了,然后还打上了石膏,那么也许当六个星期后去除石膏模型时,那人会发现他的腿无法动弹。也就是说,他的腿不再在那里了:他已经丧失了移动腿的能力,同时,当他丧失移动的能力时,他也不再拥有这条腿了,他必须依靠逐步学习并建立相应的本体感受才能重新拥有这条腿。[11] 因此,运动是储存在塑性身体结构中的一种抽象能力。梅洛·庞蒂把这称为“抽象运动”,或者虚拟运动。[12] 因为运动总是存在,并必须借助行为来实现,所以身体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来都不休息。另外,人的每一次行为都被记录在像果冻一样的塑性身体结构中,以便形成固定的习惯。比如像笔者房间的门必须猛推一下之后才能用钥匙打开,所以在笔者每次用钥匙开门前都会下意识地去推一下门,即使当时笔者在做其他事情。梅洛·庞帝也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运动的获得:某个女人戴着顶大帽子,帽子上插了根羽毛(估计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她进门的时候,她低下了她的头。她并未有意感觉到自己头上多了50cm高的东西,这完全变成了她行为的一部分。[13]
综上所述,斯普布洛伊克认识到,空间是知觉的潜在场所,是知觉的行为范围,所以,空间与本体感受密切相关。斯普布洛伊克以博物馆建筑为例,分析了博物馆作为一个建筑通常是什么样,分析了博物馆中的哪些方面与此问题相关。正如通常情况所示,楼板(地面)是垂直的,而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这个面上,建筑师也都在这个面上规划所有的运动。另外还有墙:墙是垂直的,与地面垂直;墙上挂着用于博物馆展览的画,所以墙就是我们观看(展览作品)的那个面。这说明墙与水平面在一般建筑师眼中是分离的,不是同时面对和处理的。也就是说,这座建筑是笛卡儿式的建筑:它强调的是我们看的部分与我们运动的部分之间的分离。在这里,建筑师把知觉和行为完全分开。另外,构成博物馆的砖块沿着重力方向(垂直方向)一块接一块的上下排列,所以砖的排列方式明确形成了站的姿势,即身体的站立姿势。所以,形成的这种姿势既不允许人们弯腰扭曲,也不允许人们跳动平躺,否则就无法看见墙,这让人像一根柱子。从上面这些描述中,我们会发现,这种绝对被动的身体概念实际上直接与另一个观念有关:即看一直都被用来衡量自己的身体与水平向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与各种水平信息的对应。实际上,如果再进一步说明,这种情况不仅与笛卡儿的身心分离观念有关,还与笛卡儿分离主客体、身体与世界有关。[14]
另外,斯普布洛伊克还对两项著名的实验作了深入研究,以便对视像、空间和身体产生更细致和深入的认识。其一是德国神经学家黑尔德和海因所做的两只猫的神经学洞穴试验(the neurological cave of two kittens);其二是法国考古学家让·克劳茨和威廉姆斯[15] 研究的洞穴岩画。
第一项研究是一个试验。当然,这个试验的环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洞穴,只是一个80cm直径的圆筒,圆筒内表面画了黑白相间的竖条纹。筒中间竖了一根柱,并在柱子上做了一个小尺度的天平。然后,那两个科学家在天平的两头挂了两个吊篮,并在每只吊篮内都放了一只一个月大的小猫,一只猫的脚可以沾地,另一个猫则不能沾地。因此,当一只猫跑动时,另一只猫也会随之转动,但是,它们的视觉体验却是完全相同的。两三个星期后,当小猫的神经系统逐渐成熟时,科学家将两只小猫都从吊篮中放出来。结果,脚沾地的小猫运动的时候非常正常,可以灵活地应对周围的环境,但另一只小猫却好像变成了瞎子,总是会撞到眼前的任何东西。[16]
从这项试验中,斯普布洛伊克发现了运动和视像之间的紧密关系,发现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之间的紧密关系。这项试验说明,没有动就无法看,没有看也无法动。这个试验意味着在内部和外部定位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区别,在水平直线和垂直曲线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两者都被整合到一个系统(身体)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实际上总是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或者总是在两者之间徘徊。我们不是处于要么走直线要么迷失方向的二选一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将各种线弯曲、调整和矫正的状态,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碰到或多或少的弯路才能为自己更好的定位。只有当我们运动时,我们才会看,没有其他的选择。
第二项研究是一项克劳茨和威廉姆斯所作的研究。他们研究了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最重要的一些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17] 针对这些岩画,他们划分出影响当绘制岩画时意识转变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盲点”影像,比如当一个人偏头痛或者发疯时头脑中闪现的Z字形。这类影像曾被许多人详细描述过,比如某些频临死亡时的人所看的情形,或是在服用迷幻药时看到的情形,或者在长时期感觉剥夺(比如长时间关在黑房间中)时看到的情形,或是在热歌狂舞(这是萨满最基本的经历)时看到的情形。第二个阶段是“翻译”阶段,这些影像被大家更为熟知的影像所代替和延续,比如在2万年前,一个Z字形被“翻译成”蛇的画像。第三个阶段是克劳茨和威廉姆斯称之为“漩涡”或“漏斗”的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的洗礼后,也就是经过了一条“漩涡”或“漏斗”形的螺旋隧道后,一个人便进入了真实和非真实无法分离的世界。萨满至少要达到“翻译”的层次,即变形的层次。只有在这个层次中,萨满才能把岩壁上绘制的野牛或狐狸变成真实的野牛或狐狸。
为了实现上述过程,旧石器时代的人们认为必须让这些岩画浮在岩石上,而不是固定在某个框架内,否则,绘制的野牛或狐狸将不能成为变成真实的野牛或狐狸。克劳茨还发现岩洞壁画包含着一种非常有趣的特征:大量羚羊或者野牛头的图像只画了一半,而剩下的那部分画是火把由于岩石特定的凹凸不平而投射到岩石上的阴影。那些画画的人借助他们的火把来“发现”这里是野牛的一半,那里是羚羊的一半,然后再把它“画完”。
从这个研究中,斯普布洛伊克发现了一种建筑与内部物体之间的新关系。比如在一间展览厅中,我们可以把观看绘画作品的身体被算做是作品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把窗户看作是画作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筑将不再是摆设和承载绘画作品的工具,而是一种增进绘画作品效果的建筑。同时,如果要实现这样的新关系,我们必须抛弃地板与墙面之间的差别,抛弃建筑中水平和垂直之间的差别。
从研究到实践
斯普布洛伊克早期的一个设计——freshH2O EXPO展览馆设计(1997)——初步的体现了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这个展览馆是荷兰运输部、公共工程部和水利资源管理部共同委托斯普布洛伊克设计和建造的一个水上展览馆或者说是一个交互装置,以说明建筑设计、交互式媒体编辑和高技术之间的相互交织作用。展览馆位于荷兰西南部的一个岛上,各方成员花了三年的时间试图把这个东西设计成为一栋建筑/一个展览中心/一组环境,其中,借助综合的空间体验把几何形、建筑和传感触发式多媒体装置连接在一起(图1)。
这个项目是斯普布洛伊克实现“软建筑”设想而建成的第一个项目。展览馆是一种“聪明”建筑,有着自己的运行逻辑和感觉能力,会对参观者的行为活动作出反应。在室内,仔细定位的感应器与一排65m长的蓝灯相连,这排蓝灯还与一套声控系统相连。依靠几组微处理器的协调处理,地面隆起地带的灯光和声音会随着来访者的运动不断发生有节奏的变化。斯普布洛伊克在形成这个复杂结构时,先利用高端工作站运行先进的动画和模拟软件建模并不断调整形成相互交织的16支样条(spline),最后形成椭圆和半圆截面的拉长钢制蠕虫。在软件程序中,样条被定义为活性和反应性的形态——不像线条(lines)只是操作轨迹。当样条在虚拟状态下被拉伸时,将会按照由斯普布洛伊克编制的脚本程序和例行程序所决定的参数统一变形。这样就在建筑中创造了新的环境,地板融入到墙中,墙融入到顶棚中,没有任何水平的东西存在。来访者在任何时候都被置于一种矢量的状态(就是有方向性的状态),同时必须依靠他或她的运动神经系统以及触觉本能保持平衡(图2,3)。[18]
除了freshH2O EXPO展览馆,斯普布洛伊克另外一个建成实例也很好地将上述研究融入到实践中。这就是他为法国南特名为“视觉机器”(Vision Machine)的展览而设计的展示空间(1999-2000)。 [19] 斯普布洛伊克希望这个设计能提供一种与笛卡儿观念完全相反的设计,并进一步扩展他的所谓“软建筑”设想。斯普布洛伊克对两项试验(小猫试验和法国洞穴)的研究,以及他对神经学知识的研究构成了这个设计的出发点。他称这个设计为“湿网格”(Wet Grid)。在他所设计的这个展览空间中,展览、图像以及所表达的建筑思想都是完全不同的(图4)。
斯普布洛伊克说:
当我看到这些图像时,我只看到一种东西:漩涡。漩涡在艺术史和知觉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艺术史和知觉史也是围绕着垂直轴线而组织,同时,当漩涡与知觉产生联系时,漩涡就是眩晕(迷失方向)的轴线。眩晕是人身体的属性,尽管有时让人感觉是在天堂,但更多的是在地狱。人们在处于上下翻转的时候,会描画出很多螺旋结构式的视像。让我们想想赫胥黎写的《知觉之门》——或者各种临死体验报告,都是纯粹的精神治疗之旅。身体的漂浮总是与种种非正常视觉形象联系在一起,比如颜色会绚丽明亮很多,每样东西都在发光,进入纯粹的快乐状态。所有看到的景象都包含了发光的东西、金碧辉煌的宫殿和镶满宝石的河流,等等。[20]
斯普布洛伊克的这个设计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站立的姿势决不是促使身体去看的惟一的姿势。他认为,通常在建筑中,水平视像是外部定位的视像,而在这里,眩晕视像则是内部定位的视像。水平视像将为自己定位,可是眩晕视像会让一个人迷失方位,走进所谓“螺旋的迷宫”。[21] 当然,正如上文提到的,斯普布洛伊克认为他并不完全处于上述两个方面的任一方,他认为自己“处于这两者之间,而且总是位于这两者之间”,因为他认为法国科学家瓦勒拉曾说过:“间状态是最基本的立场” (图5,6)。[22]
在具体解释“湿网格”时,斯普布洛伊克认为网格是建筑中最古老的工具之一。如果一位建筑师想创造比如从某个视点的秩序,那么他就要跳上一架想像中的直升飞机,然后在那个地方的上空投下一片网格。这种行为源自于某种军事行动。网格与自上而下的观察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与自上而下观察的秩序和属性也有着直接的联系。网格完全不同于我们如今称之为网络的东西。实际上,“网格”和“网络”这两个术语呈现出的都是“图解”,都是解释性的图解,都是文字上的“观察”,都是表达概念的直觉图案。斯普布洛伊克认为,
网络呈现的是现有秩序,呈现的是当代社会的自组织状况。因此,网格的位置处于将秩序自上而下强加于物体之上的地方,而在网络的视角中,秩序出现于物质交互活动之外:即出现于处于混乱边缘的模式、稳定性和秩序之中。[23]
斯普布洛伊克认为,“湿网格”的位置处于网格和网络之间,非常接近于“液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秩序既不是晶体的固态,也完全不是“自由”流动的液态。一方面,液态没有足够的凝聚力,不能形成整体的活动。另一方面,固态晶体是一个整体,但是不能流动,因为晶体只有一种固定的状态,所以固态晶体只能在稳定不变的条件下存在。与这二者不同,“湿网格”意味着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表面的状态,既不是一维的也不是二维的状态,而是策略上的“间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比上述两种状态都强大。另外,这种“间状态”不是液态和固态各占一半的中性状态,因为其属性决定了其不是均质状态,而必然是一种多维的异质聚合体。因为结构的属性中包含了时间的流动,所以网格的软化会造成网格的变形,并会促使其比以前的硬网格更为强大(图7,8)。[24]
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斯普布洛伊克也应用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设计程序,一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设计程序。斯普布洛伊克将计算机主要看作是一种图形形成工具,而不是绘图工具。具体而言,他利用计算机先从某个系统内部演化出某个图形,然后,再把这个图形加入到另一个系统中,最后再从这个系统中将上述图形演化成一个新层次的图形。
这种设计过程完全不同于设计中标准的从“绘图”到“现实”的工作过程。斯普布洛伊克认为,一般来说,建筑师在设计中总是在创造各种图解,比如概念图解(比如草图)、信息图解(比如绘图中设定线的粗细)和表意图解(比如指南针),(如果我们看看传统建筑师在0.3铅笔、针管笔、粗铅笔和签字笔之间是如何转换的就可以理解这三种图解)。建筑师借助还原的方法由繁到简不停的画图,从大部分都是欧氏几何图形的模糊草图一直画到清楚明显的单线轮廓(施工图)为止,最后确定每个建筑元素的位置。
斯普布洛伊克的工作方法与之完全不同。因为在计算机中模糊线和单线的绘制都被编制成了程序操作,所以对斯普布洛伊克而言,曲线的移动(正如手绘草图)不是由他本人来完成,而是由计算机来完成。正如斯普布洛伊克所说的:“计算机图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不仅仅是在处理过程中,(我)喜欢和厌恶(某种形态)变成了某个软件中的简单程序,而且还可以把这种方式作为确定某种运动的基本方法。”[25] 按照他的理解,计算机在建筑学中的应用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计算机曾(现在也还在)被用作实现完美形状的梦想和自动运行的设计(这似乎只能产生雪花形状的教堂和二流的柯布西耶);更糟的是,计算机还曾被用作梦想漂浮在赛博空间中的建筑;但是,这样的时代即将结束。对于建筑专业而言,关键在于计算机已经不再适合被局限在数字绘图(计算机绘图)的天地中,因为在数字绘图中,真实的设计仍然远离机器,仍然要依靠手绘,依靠天才进行引导。” [26]
在具体操作中,斯普布洛伊克先将现在的展览所在的那座建筑看作是典型的古典主义的中心/外围关系。外围是水平向柱廊,中心是垂直向中厅,中厅的顶部有一个穹顶,人们可以透过穹顶的天窗看透过屋面洒下的光。
然后,在计算机中,斯普布洛伊克将8对双线放在原有建筑的底平面上,从入口一直穿过整栋建筑。然后,他引入一个他称之为“舞蹈设计”的软件程序中,并将4组“漩涡力”置于8对双线所在的底平面中。那个软件程序就像一只手,可以按照不同参数及时调整4组漩涡的运动。不少好莱坞电影都利用这个软件制作电影中的龙卷风,比如电影《龙卷风》。这套软件非常强大,可以模拟龙卷风卷动泥土、汽车和牛的场景。斯普布洛伊克用这个程序来形成所需要的运动和姿态,但是,这个程序不会改变8对双线的骨架。正如他所说的,“这个过程更像指导四位舞者分别跳出特定形态的旋转动作——只不过在跳舞时用了一根弹力带将他们联在一起。这个过程改变了个体运动并会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新模式。”[27]
然后,斯普布洛伊克在研究了这套系统的变形模式并估计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可能性后,调整了骨架中某些缺陷,而后进行运算,而后再进行调整,一直调整到所有骨架都符合他的意图为止。我们可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过程:从原有建筑的入口处一直到中厅空间的末端总共有8对线,先让三对线形成一个结,然后这个结再分裂出导向左边的两对线,同时还分裂出导向右边的一对线,这对线又形成中厅右边的另一个结,然后,又将这个结连到另一组线上。当然,实际的操作过程比这个更复杂,但是却基本归纳了这个设计形成的一般性思想,根据这套思想可以形成一套双线构成的软网格。一般来说,网格由两个相互垂直的系统构成(X方向和Y方向的合成),但是,这个网格却是某个纵向系统的横向运动而形成(Y方向系统受到X方向的力变形而成)。
然后,这些线在漩涡力的影响下产生不同方向的扭曲,并形成最后的面和空间:一条线移动时会形成面,各个线分离并扭曲时会形成空间。因此,结构体并没有围合空间,结构体的扭曲就形成了空间。这是设计、绘画和图像中非常关键的部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每幅画都无法90℃垂直摆放的,而地面的任何部分也都不是90℃水平的,除了处于漩涡的外面。同时,在摆放每幅画时,也会根据结构体的走势来处理,这样,观众在看画的时候,就不会仅仅在水平方向产生视觉感受,还会做出各种姿势。
最后,要强调的是,这个设计尽管开始于8对随着漩涡力产生变形的双线系统,而后这些线相互交结形成“结”或者相互分离,而后形成面和空间,但是,这些线在建成结构中并没有结构作用,正如斯普布洛伊克所说的,“这些线的存在只是为了吸引知觉和运动,但却不产生垂直方向的作用”。[28] 这与通常的做法完全不同:通常我们都是在线上布置柱子,然后再调整柱子的形态。斯普布洛伊克认为这是最糟糕的方法,在他这里,结构形成(或变形)是建筑师分析知觉和行为之后产生的结果(图9,10,11)。
这个设计的整个生成过程与德勒兹关于造剑的分析很有类似之处。在德勒兹所著《千座高原》中,他说,
你不能从一块金属板中切割出一把剑的轮廓。你必须加热金属板,弯曲它,折叠很多次以便让这把剑有弹性,同时,到最后,你必须突然冷却这把剑,这样固化才能形成更锋利的剑锋。所有的操作和调整过程都是制剑所必需的。一把剑决不是由均质的材料构成,而是曾经有过各种材料形态,材料本身就包含了某种运动过程和某种结构特性,你必须协调好这两者才能造出一把好剑。[29]
斯普布洛伊克的设计“灵感”来自他对建筑相关学科和知识的研究。他的设计实现了肉体和空间、物体和速度、表皮与环境之间的无缝结合,并把平面和体积、地板与隔板、表面与界面相互融合。他反对传统的机械论式的惰性肉体体验,赞成更加柔性和更注重感受的环境设计。在这样的柔性环境中,人的行为、空间感受和空间的视觉效果得到了全面的综合。这种“软建筑”一方面将挑战传统建筑感知的笛卡儿几何基础,另一方面还会引进其他种类的身体感受模式,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新的建筑设计领域。
设计作为研究
从以上对斯普布洛伊克设计过程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设计是建立在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研究基础上,并由之引发。不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操作过程上,这样的设计都不同于以建筑师的个体“经验”或以创造奇异形式作为主导的设计过程。按照斯普布洛伊克的说法,他的设计更像是烹调:烹调需要技巧和配方,但是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却不能被完全预知。也就是说,“我们应在开始就把事物看作是动态的(并摆脱建筑作为‘创作’的道路),这会涉及到现在非常著名的自组织概念。在自组织中,材料就是活动的媒介(agents),媒介寻求的是效力(agency)而不是其他,寻求的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并不是以直觉为基础预先建立的,而是自下而上出现的。”斯普布洛伊克将他的设计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一,选择一个系统,并为以这种选择为基础的设计创造一种架构(configuration);二,让这个系统中的各种元素和关系动态化;三,最终统一这个系统;四,变形并产生建筑形态(morphology)。简要地说,就是从系统到可塑性系统,再到刚性系统,再到形态的过程。在最初的集中阶段,有一个加速,即一种拓扑动态化的过程,就像穿越了一条非常窄的通道。而后,这个过程会慢慢减速,并通过分叉形成某种几何形式而停止。具体而言,以“视觉机器”展览设计为例,首先,我们要按照经验看看所设计建筑物真实的总体情况,然后要反思相关的建筑类型(我们不能去建立一套垂直架构的组织,而是要建立一套水平架构的组织);然后,我们需要先考察各种各样的展览机制(展览作品与参观者之间的关系),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多样性和差异(运动与视觉的关系),为它们绘制地图并进行组织(各种“看”的可能性),考察它们的内在关系,考察它们的内部剖面,考察现场并绘制相关的图示(原有建筑的入口处一直到中厅空间的末端的8对线);最后,将分析研究所得到的类型动态化和拓扑化,而不是仅仅从某处引入某种拓扑图形或系统(利用“舞蹈设计”软件将已有的各种组件扭曲产生变形)。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对软件的利用只是各种实现设计的方法之一,我们既可以选择其他软件,也可以选择数字技术之外的操作。比如在斯普布洛伊克另一个关于高层建筑的设计中,就是利用实物而不是完全用软件来完成设计:首先,将一组垂直方向的毛线浸入水中,而后,这组毛线会自组织形成某种复杂结构系统,最后利用软件进行模拟。这也正是分叉的意义所在。[30]
总的来说,斯普布洛伊克这种试验性的设计在建筑学的发展中似乎还处于某种非主流或另类的位置。然而,如果将他的做法放在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不断尝试新的试验和研究的做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大规模的开展研究和开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工业和政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工业和市场领域的领导者们每年都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思想(微软现在每年投入10亿美元来探索研究新思想)。10年前,美国的大学(某些大学仅在一个研究机构中就雇用了上千名研究人员),极大地改变了高校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并为跨相关专业之间开放的信息知识交流创造了全新标准。而这也成为当代建筑新实践的普遍标准。例如,弗兰克·盖里事务所中专门的研究和开发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将航空工业中的技术转换到建筑应用中。福斯特及其合作伙伴、阿鲁普(Arup)事务所,以及OMA事务所也建立了类似的团队(OMA建立了自己的姊妹公司AMO)。实际上,在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研究和实验一直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普鲁夫(Jean Prouve)很早就开展了与法国航空工业的合作,并创造出最早的所谓“高技派”建筑。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很多设计,也都是因研究和试验而引发。[31]
在当代建筑教育中,由设计研究而创造的试验性形式,也日益开始占据更多的比重,斯普布洛伊克就是典型的实例。实际上,在现代主义建筑教育中,这种对试验性研究的兴趣就已经出现。比如,包豪斯当时的教学核心就没有放在“建筑”问题上,而是放在新工业进程、新媒体和新制造上。包豪斯在最初8年中并没有单独的建筑课程教学。这种教学设置主要来源于凡·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在魏玛创建的课程设置。维尔德认为学生设计只要通过严格分析项目中的各种问题就可以完成,而不是通过应用预先设想的设计规则而完成。20世纪30-40年代以后,这种信念在某些学校得到了系统化的发展,比如乌尔姆的设计学院(Hochschule fur Gestaltung)。20世纪70年代,大量建筑教育实验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包括(被大量复制的)阿尔文·博雅斯基(Alvin Boyarsky)在AA开展的教学活动,还包括洛杉矶的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海杜克的纽约库伯联盟,里伯斯金的匡溪学院,还有埃森曼位于曼哈顿的IAUS研究所。这几个学院的发展都是高度独立的,但在实验形式上都比较严格和系统。在当时传统的大学机构中,像文丘里或柯林·罗这样的教育家实际上也都已经脱离了20世纪60~70年代传统的设计工作室模式。他们追求的是设计研究,他们带领学生付诸行动,并涉足了更广阔的领域。而这些研究最后都成为《向拉斯韦加斯学习》和《拼贴城市》的主要素材。实际上,近期库哈斯的“哈佛城市研究计划”也延续了这套路子。[32]
不过,这些富于创造力的试验在过去和现在都被排除在专业建筑教育的统一标准之外。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建筑师的形象一直被虚构为精力旺盛的“有创造力的个人”,长盛不衰。世界范围内的建筑学院仍然固守于那个令人着魔的信念:发展个体设计师的创造性和自主性。随着20世纪60年代路易斯·康的声名远扬,这种信念也发展到了顶峰。[33] 现代建筑追求“个人化”在教育上的持续巩固,反映出建筑专业对具有鲜明特征风格的神魂颠倒,而一对一的学习模式在根本上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迷恋。布雷特·斯蒂尔(Brett Steele)认为,这种像治病般的学习模式(再加上学生与老师之间通过面对面交流而取得的假想“经验”)已经成为最糟糕的教学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主要后果就是设计师的专断独行。主观性(subjectivity)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令人讨厌的概念,现在许多人都试图打破这个概念,以便把学生、教师、设计工具,特别是代表设计师“身份”(identity)的任何概念,都处理成本来就处于不稳定和多样的状态。[34]
建筑学科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学科,它更需要创新和试验。按照布雷特·斯蒂尔的说法,专业性的设计学科,最初只是17~18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事业的产品,而后在19世纪的学术发展下才得到了系统化的进步,最后在20世纪初才实现了现代化和大规模的工业化。也正是从那时起,建筑学科开始慢慢习惯于越来越稳定的内在发展形式。 [35] 因此,建筑学科要想在21世纪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研究和试验自身,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
(衷心感谢冯路先生的建议和支持。)
注释:
[1] [2] [3] [4] [5] [6] [7] [31] 参见Zellner, P: 1999, Hybrid Space, Thames&Hudson, London,pp120~117
[8] [9]具体论述见《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奥立佛·萨克斯著,孙秀惠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6。奥立佛·萨克斯是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的神经学教授。他擅长以纪实文学的形态将脑神经病人的临床案例,并被誉为本世纪难得的“脑神经文学家”。
[10] 这个例子转引自Leach, Neil(ed.):2002, Designing For A Digital World. Wiley-Academy, London,P93
[11][12][13][14][17][19][20][21][22][23][24][25][28][29] 参看Leach, Neil(ed.):2002, Designing For A Digital World. Wiley-Academy, London,pp94~97;这里的赫胥黎(1894-1963)是博学的英国作家,是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瓦勒拉(Francisco J. Varela),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法国巴黎理工学院的认知科学教授。萨满是指某一特定部落社会的成员,萨满是现实世界和不可见精灵世界的中介者,他也为治疗、神示或自然事件的控制而施行魔法或巫术。
[15] 让·克劳茨(Jean Clottes),法国史前古迹研究学家。威廉姆斯(David Lewis Williams),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岩石壁画研究所的人类学教授。
[16][18][26][27][30]参看Spuybroek, Lars: 2004, Machining Architecture, Thames & Hudson, London
[31][32][34][35]参看Steele, Brett, "P2P intelligence, or learning from Kazaa" in Architectural Review Australian, no.090, p59。布雷特·斯蒂尔是AA 设计研究实验室(DRL)的主任。
[33] 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路易斯·康在宾大任教,宾大建筑系曾收到过多达1200份的年度入学申请,以至于学生录取不得不采用抽奖的方式。具体描述参见同上p59,116 |
|
纯粹建筑 | 理想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