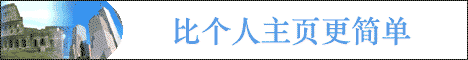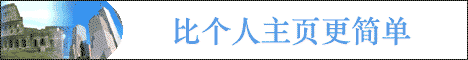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07-05-27 12:15:14
□ 阅读次数:34279
|
|
|
亨利·列斐伏尔研究
汪原
|
【摘要】亨利·列斐伏尔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理论家。本文通过对其主要思想的介绍和评论,试图阐明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理论对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等学科的影响,揭示出现存的与空间相关的理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
【关键词】空间生产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象空间
Abstract: Henri Lefebv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kers in 20 century. He addressed intrinsically relevant to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every day life and the nature of space. The article analyses his critical role in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from the 1920s to his death in 1991.
Key Words: production of space, spatial practi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中,亨利·列斐伏尔(图1)关于日常生活和空间的理论也许与城市和建筑研究联系的最为紧密。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之一,他在《论国家》和《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等著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早已被国内学者所熟识,但他关于空间的研究以及对相关学科的巨大贡献,却一直被国内研究者所忽略,这一状况与英语世界对列斐伏尔的认识极为相似[1]。尽管如此,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爱德华·索加(Edward W.Soja)仍然这样评价列斐伏尔:“1950年代以后,他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屈一指的空间理论家,并成为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最强有力的提倡者”[2]。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列斐伏尔不仅亲身参与激进的艺术和社会团体的活动和实践,而且其著作对城市化、城市空间以及建筑理论也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他的思想不仅在法国促生了对现代规划方法和建筑功能主义的广泛批判,而且对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规划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思想历程
列斐伏尔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法国的哲学家。他不仅向法国知识界翻译介绍马克思的思想,而且还发表了大量文章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进行阐释。1928年,列斐伏尔与一批年轻的哲学家创办了法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刊物《马克思主义杂志》;192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39年,列斐伏尔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一书。该书不仅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形式逻辑的超越,肯定了黑格尔试图通过辩证法将理念和内容、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思想,而且趋向于在实践活动中用辩证法去解决各种矛盾。并在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全面的人”的思想基础上,引申出“总体的人”(Total Man)这一概念,认为人类终将实现其所有的潜能而成为“总体的人”[3]。
战后,列斐伏尔出任图卢斯广播电台主任一职,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一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述。其中,列斐伏尔在对青年马克思诠释的同时,还大胆地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他认为异化是人类实践的基本结构。在总体上,每个人的行为都由原始自发的秩序、理性的组织结构和压抑的拜物教系统三个发展阶段组成。据此,在经济学上,劳动的分工导致了工人的被剥削;在政治学上,有效的管理最终腐化成国家专制(政党专制)的工具;在哲学上,思想的阐明最终变成严酷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统治的工具。
二战后法国知识界的状况非常严峻,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往往超出了理论和思想范围,有时甚至沦为对人生的攻击,列斐伏尔也没有免俗。[4]这也一度使列斐伏尔陷入极其困苦的境域中。一方面,他要应对来自党外各种思想的讨伐,另一方面,由于他偏离主导路线而不断遭到党内人士的批判。迫于压力,列斐伏尔只好暂时放弃哲学而转向了社会学研究。
在当时,法国的社会学研究并不带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并且大多集中在非教学的研究机构和政府规划部门。但在法国,从事社会学研究需具有相当的哲学素养,因而列斐伏尔很快就完成了学科角色的转换。凭借马克思主义思想框架,列斐伏尔对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社会语言学以及日常社会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并被法国社会学界公认为这些领域的奠基人。
1956年,列斐伏尔重返哲学论坛。在与合作者创办的《论证》杂志中,给自己规定了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同时与东欧的共产运动和法国的非共产信仰的知识分子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势力。1958年列斐伏尔终因对斯大林及其法国追随者的无情批判而被开除出党。
在这段时间内,列斐伏尔的生活非常窘迫。出于生计,他曾经在巴黎街头开出租车,也正是由于这种生活状态,使其对城市和日常生活有着十分深入细致的观察。当然,被开除出党并没有影响列斐伏尔的研究,反而激活了其思想创作的激情。在随后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他的思考涉及了哲学、社会学、文学分析和诗学以及建筑和城市科学,在理论上他不仅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且还吸收了后结构主义的思想策略,使其思想带有了较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在20世纪中期,法国知识界分为两大阵营:其一是处于上升势头的结构主义,其二是日渐势微的存在主义。由于列斐伏尔人道主义思想和对青年马克思的推崇,他很快就成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敌之一。他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等人是技术主义的护教论者,批评他们试图创造一套新的技术语言来分析问题;批评福柯对辨证主义历史和主体性的拒斥,批评德里达抬高书写贬低言语;他还批评阿尔杜塞建构了一种与实践相脱离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消除了人民大众的创造性,无限放大了知识的或少数知识精英的作用和权力。他将结构主义看作是对政治的逃避,是技术理性在知识范围内的扩张,缺乏任何行动的激情(“结构不上街”)。
1968年,红五月事件席卷欧洲和北美,这次运动似乎印证了列斐伏尔的预言。他将学生看作是社会和理性异化的牺牲品,看作是社会解放、实现“总体人”这一终极目标的代言人。作为巴黎第十大学的教授,他对学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列斐伏尔提出的“改造生活”、“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让日常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等在“五月风暴”中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因此,他也被称为“法国学生运动之父”。
在1950特别是60年代,列斐伏尔与各种艺术团体的接触和合作对其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情境主义。一方面,情境主义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中借用了大量的思想,另一方面,情境主义积极参与空间的试验激发了列斐伏尔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并引向了全球性城市化的批判。列斐伏尔特别赞赏荷兰建筑师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is)的新巴比伦方案(图2)。在新巴比伦中,康斯坦特以一种对迷宫式空间的使用摆脱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功能主义,而且其介于公寓综合体和城市之间的适宜的尺度,使列斐伏尔看到了打破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分裂、促进新社会变更的希望。
在1960年代,他与另一前卫组织Utopie Group有着密切的联系,该组织由多学科的人士组成,并创办了以Utopie Group为名称的刊物。此时,巴黎到处充斥着巨型建筑,德方斯的办公大楼就像是技术理性的凯旋门。据此,刊物刊登了许多讽刺性的漫画和滑稽的言论以构成他们对城市以及法国文化实践的革命式的批评。受到情境主义和英国的阿基格拉姆学派的影响,Utopia Group组织中的建筑师提倡一种瞬时的建筑,作为创造节庆的和愉悦的环境的方法,这种环境就是他们认为的空想共产主义世界的到来。但是,该组织在空间视觉与政治计划之间本来就很纤弱的联系很快就消散了,《Utopie Group》也变成进行批判的纯粹文本论坛,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即是“否定的乌托邦”。
尽管深受这些艺术运动的吸引,但是列斐伏尔始终坚持卑贱的、平常的、鲜活的和可接近的艺术,坚持大众主义,反对感伤或简单粗暴式的革命艺术,而对真实性的坚持也导致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争执。当认识到幻想的方案不足以改变平凡普通的生活时,列斐伏尔将其对日常生活转化的任务从前卫的审美实验转向了对城市规划策略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的黄金年代,列斐伏尔的著作也成为抢手的读物,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这时列斐伏尔的主要精力已转向了城市。在短短的五六年中,列斐伏尔出版了七本专门讨论城市化和城市空间问题的著作。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了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空间的生产》(图3)。在书中,他不仅对空间问题进行了思考,而且不断对二元论逻辑进行了解构,将处于边缘的各种关系重新结合,发展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并以空间为基础,对日常生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消费社会、城市权利、主体意识的城市化、城市变革的必要性、从本土到全球范围内不平衡发展等问题作了广泛的考察和论述。
1991年,列斐伏尔去世,终年90岁。纵观列斐伏尔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其生活故事既是时间性和社会性的,同时也是空间性的,这也使得列斐伏尔对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social being)之间的三重意识(tripleconsciousness)具有了更为具体的时空意义。我们或者可以用空间的生产、历史的创造和社会关系构成来对应这三重意识。在他90年的生命旅途中,这三重意识有过许多不同的转折和变化,从早期迷恋超现实主义和工人阶级意识,到对日常生活以及城市现状的空间性和社会学作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再到晚期对于空间的社会生产的研究,他的一生始终正如爱德华·索加所指出的“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知识分子‘流浪者’,一个来自边缘却能在中心生存并且兴旺发达的人”[5]。
二、日常生活批判[6]
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1972年发表的“日常和日常性”一文,是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的总结和概括。[7]
由于列斐伏尔拒斥对概念作任何静态的分类,因此对日常生活并没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他试图通过大量的描述将其显现出来。其中最根本的是真实的生活,“是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里和环境,……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物质文化”。[8]但这种重复性的、数量化的物质生活过程又具有一种“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气氛”。列斐伏尔指出,“在日常生活的本质特性之中内含了丰富的矛盾性。当其成为哲学的目标时,它又内在地具有非哲学性;当其传达出一种稳定性和永恒性的意象时,它又是短暂的和不确定的;当其被线性的时间所控制时,它又被自然中循环的节奏所更新和弥补;当无法忍受其单一性和惯常性时,它又是节庆、愉悦和嬉戏的;当其被技术理性和资本逻辑所控制时,它又具有僭越的能力”。[9]
列斐伏尔是在1936年出版的《被蒙蔽的良知》中首先提出日常生活概念的。在这部以批判法西斯主义、个人主义等神秘化的意识为内容的著作中,提出了要从描述日常生活中最平淡无奇的生活开始,寻找出一种贯串于日常生活的分析模式。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日常生活概念是作为超越生产、阶级斗争和经济决定论而扩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既能包含更多的哲学意义和范畴,从而对异化作普遍深入的分析,同时又能超越诸如劳动、社会组织等特定的功能范围,达致没有明确定义的、所谓剩余的或边缘的范围。
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他将当代的日常生活和前工业时期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比较[10],他认为前工业时期的日常生活具有区域的多样性和地方的同一性或整体性等特征,具有一种下意识的形式。19世纪的日常生活缺乏这种整体的形式,理性化的增长带来不断的分裂。在二战后的十年中,技术和官僚的统治已经渗透到几乎每一个存在领域,导致了功能的特殊性、社会分化和文化被动性的不断增加,家庭生活、休闲时间或文化活动的几乎每一个层面都无法逃脱系统化,这种无情的理性化在当代城市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和生动。
战后的快速重建和以及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出现的新城,特别是在离其家乡不远的区域发现了一座天然气田而突然出现的新城Mourenx(图4)与家乡牧歌式景象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对列斐伏尔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心理失落,也迫使列斐伏尔将城市主义作为当今关键的文化问题之一,从而构成了其思想的重要转折。在列斐伏尔眼里,Mourenx新城所呈现的是一幅城市和城郊匀质化的凄黯的景象——匿名的、巨大的集合体占据着城市周边,平淡和重复的办公楼、沿着山腰不断扩展的郊区别墅就像成百只在巨大橱窗中的死鸡。他不仅认为Mourenx像沙漠一样的空间扼杀了任何公众的自发性和游戏的品质,而且将这种无情的匀质化与美国化等同起来,将这种现象视作潜在的全球现象。
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的思想比德·赛图(Michel de Certeau)更为悲观。[11]尽管如此,列斐伏尔对日常经验压抑的强调被一种先验的信念所支撑,这种信念是日常生活不能被官僚政治的管辖所容纳,这种信念怀有生成转化的欲望,例如自然、爱情、简单的家庭愉悦、庆典和节日都会侵蚀任何总体的、静态的系统化。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卷中,列斐伏尔对乡村节日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阐释,他将农民的节日看作是愉悦、自由和日常生活社区感的显示,并可以提供一种更为持久和有意义的方法。[12]
列斐伏尔预想了一个丰富充裕、有更多的休闲、在日常欲望和需求之上的个体解放的社会。这种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但仅仅是片刻的。
当《日常生活批判》的后两卷关注官僚和“控制的”消费对社会的不断占领时,列斐伏尔辨证的思考则传达出乐观主义的态度。其方法不是确定对立双方以形成新的综合,而是一种对多元张力的叙述,这种张力所形成的转化力量是无法预期的。对于列斐伏尔来说,总体性不是从自身外化出的产物,而是向未来开放的一种具体现实。由于日常生活包含了主体对压抑的最直接体验和最强烈转化的潜在性,因此对于主体实践和客体决定论而言,他对主体实践更感兴趣,而乌托邦就是这种实践的本质的组成,乌托邦不仅可以提供各种选择的可能、引导无止境的试验,而且个体和集团还可以积极发动社会的转化过程,以建构新的未来。而对于社会转化来说,日常生活比工作本身更有意义,这也是列斐伏尔能够与情境主义合作的思想基础。当然,与情境主义信奉情境的潜在性和革命的瞬时性不同,列斐伏尔相信革命的变化是一种缓慢和全面的过程,很少戏剧性和个人性,是根植于日常生活的一种长期的历史实践。
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思想中,对女性的体验有着敏锐的分析。他认为尽管日常生活对女性产生着巨大压力,但日常生活仍然为女性王国提供了幻想和欲望,提供了声讨和反抗,提供了在官僚系统化之外新的竞技场。因此,消费社会对于女性生活来说扮演着魔鬼和解放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消费对女性形成了压抑和控制,使其在性别客体化中丧失体面;另一方面,消费又不能完全被理性化所承载,具有不可通约性的欲望保留了一种自发的意识,因此也就潜藏着希望;在空间上,随着透视法的出现和运用,技术理性占据了主导,空间的女性品质被逐渐压缩;在时间上,女性与周期性的时间,如自然的节奏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女性具有一种先天的抵抗系统化的能力。这些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众多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大众文化与女性对公共空间占有问题的探讨。
三、空间理论
与后现代哲学家对空间问题探讨所不同的是,列斐伏尔有着更为系统和完整的空间理论。在对二元论的空间理论,即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提出了质疑的基础上,他首先对现代认识论将空间视作“精神的事物”和“精神的场所”的趋向进行全面的考察,并对以往完全从几何学角度把空间说成是“空洞的空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空间观致使现代认识论把空间看作是精神性的东西,从而使研究者可以主观随意为空间附加各种意义,以此为基础的空间研究必定缺乏分析性和理论性,其描述的也只能是空间的某个片段,也绝不可能促成关于空间的完整的知识。因此,必须对物质领域(自然界)、精神领域(逻辑的和形式的抽象)以及社会领域进行统一性的理论阐述,据此,我们就可获得空间的无限多样性,即一种空间与另一种空间的重叠,从而建构出一个共同的平台,使研究者可以从各自不同的学科出发对每一种空间加以研究。当然,列斐伏尔的统一性思想并不蕴涵某种特殊的语言,它不是一种元语言,而是强调空间解码活动的辩证特征,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13]。
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核心,是生产和生产行为的空间化,用列斐伏尔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品”[14]。即空间,在现有的生产模式中作为一种实在性的东西而起作用,它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商品、金钱和资本既相似又有明显的区别。首先,空间应当被看作是服务于思想和行动的工具;其次,作为一种生产的方式,空间也是一种控制的、统治的和权力的工具;另外,空间并没有被完全控制,它能够形成各种边缘化的空间。据此,列斐伏尔从四个方面展开了对空间的分析。
第一,物质(自然)空间正在消失。在总体上,自然空间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社会过程的起源和原始模式的基础。自然空间的消退不仅发生在物质环境中,同样也发生在人的思想中。因为,人类对于什么是自然、自然的原有状态等问题已不再关心,自然界的神秘力量也只是被转释为科幻的或迷信的世界,自然已经沦为各种社会系统塑造其特殊空间的原材料的产地。
第二,任何一种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特有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包含生物的繁殖以及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空间场所。创造过程所需要的具体场所与生产、禁忌和压制等因素相关,主导性空间对附属性空间具有支配力量。
第三,空间的知识就是对生产过程的复制和揭示,也即空间解码活动。因此应从对空间中事物的关注转向对空间生产的关注。对此,列斐伏尔区分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象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重要环节,并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辨证的考察。
空间实践通常关注的是功能形式意义上的空间,同时也包含在概念思考和体验之前的感知空间,空间实践涉及空间组织和使用的方式。在新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空间实践使日常生活和城市现实之间体现了一种紧密的联系,它关注的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既包含日常生活,也包含城市行为,涉及了从建筑到大型的城市设施等各种各样的功能空间,涉及的是一种物体和事物的空间,也是一种人在其中移动和行为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将其看作是经济或物质基础。其中,不断生产的空间形式和实践必须与不同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行为相适应,这不仅定义了场所、行为、符号以及日常琐碎的空间,符号或象征也使场所具有了特性和意义。
空间的表象涉及概念化的、构想的空间,是一种科学家、规划师和专家治国论者所从事的空间。这种空间在任何社会中都占有统治地位,趋向一种文字的和符号的系统,是一种可以据此进行控制的工具。
表象的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向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或生活的空间,是一种被占领和体验的空间,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它与物质空间重叠并且对物质空间中的物体作象征(符号)式的使用[15]。
第四,空间具有历史性。如果空间是生产的,那么必然有其生产过程,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也就具有了历史维度,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也具有至高无上的理论意义。既然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独特的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的生产。我们如何判定新型空间的出现、新型空间出现是否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等问题对我们进行历史的、社会制度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厘清了这些问题,也就厘清了相应的空间符码,也就厘清了相应的历史分期,历史学即能形成空间范式的转折,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吉迪翁的空间哲学所存在的致命缺陷。[16]
在建构自己的理论系统时,列斐伏尔运用了不同的空间概念。绝对空间:在本质处于自然状态,一旦被占领,就会相对化并具有历史性;抽象空间:与积累的空间联系在—起,在这种空间中,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相互割裂,空间呈现出工具性特征;矛盾空间:抽象空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旧有空间和新的空间的分裂;差异空间:不同空间的叠加与拼接。
总之,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认为,正是在创造和存在的行为中,空间得以现身并蕴涵其中,生命进程与不同种类的空间生产密不可分,空间的生产在本质上也就成为一种政治行为。[17]
除了现象学的纬度以外,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意识。他从逻辑上反对语言在先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过分强调了言语和书写。在他看来,任何一种语言都囿于空间之中,那些试图为语言提供全新认识论基础的人,必须注意语言的时间特性。低估、忽视或贬抑空间,也就等于高估了文本、书写文字和书写系统(无论是可读的还是可视的系统),就会赋予它们以理解的垄断权。
据此,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符号学。他认为:“当由文本组成的符号应用于空间时,人们就必须停留在纯粹的描述层次。任何试图应用符号学的理论去阐释社会空间的企图,都必须确实地将空间自身降至为一种信息或文本,并呈现一种阅读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历史和现实的方法”[18]。
列斐伏尔强调,在被认识之前,空间就已经存在,在可以被解读之前,空间就已经生产出来。因此,对空间文本的解读和解码,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表象的空间(生活的空间)如何向空间的表象(概念的空间)的转变。
列斐伏尔还向诸多的传统思维习惯发出了挑战,他指出:“即使新哲学前景广阔,但透明、中立、纯粹的空间幻象仍然会逐渐趋向消亡,我们不仅用眼睛、用理智,而且是用感觉、用身体来感受空间,这种感受越是详尽,就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空间内部所蕴涵的矛盾,这些矛盾促成了抽象空间的拓展和另类空间的出现。他要求人们应该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可读性、可视性和可理解性的谬误中解脱出来。他断言:我们已经步履蹒跚地走在了社会空间科学的边缘,这种科学决不是企图达至一种彻底的总体性、达至某种体系或综合,这一方法试图把原来风格的要素重新结合起来,并以清晰的区分来代替含混不清;把分割的元素重新结合起来,并对新的结合体重新加以分析”[19]。
列斐伏尔将自己的这种空间分析方法称为“空间学”,以便同现有的学科术语区分开来。他所提出的概念框架建立在不同的认知或分析层面上,即微观的建筑层面,中观的城市层面,宏观的国土资源以及全球性土地资源层面。因此,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是一种可以在各种尺度上展开运用的空间科学。
四、空间的生产
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的生产,始于“对自然节奏的研究,即对自然节奏在空间中固化的研究,这种固化是通过人类行为尤其是与劳动相关的行为才得以实现的,即始于社会实践所塑造的时空节奏”[20]。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对存在于空间中诸事物的研究转到对空间实际生产过程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无法将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因此这种转变对于传统思维来说是困难的。但列斐伏尔认为,由于(社会)空间的先在性,它不是空间中诸多事物中的某一类,也不是诸多产品中的某一种。空间本身不能归类,而是空间对事物加以归类,这种归类实际上蕴涵了事物共同的内在关联性,即秩序或无序。(社会)空间本身是过去行为的产物,它就允许有新的行为产生,同时能够促成某些行为,并禁止另一些行为。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这些关系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使空间显现出来,也就所谓生产出了空间本身。因此,(社会)空间既是被使用或消费的产品,也是一种生产方式,既是行为的领域,也是行为的基础。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有性,必然会导致差异性的存在。这种差异被蕴涵在空间及其矛盾之中,即资本主义社会依仗技术所形成的主导性空间与个体或集团可能拥有的自然空间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不仅如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力“三位一体”要素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也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在空间的“三位一体”中得以充分的结合与体现:首先,这种空间是全球性的……其次,这种空间是割裂的、分离的、不连续的,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区域性;最后,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包括了最卑贱的和最高贵的、被禁忌的和具有王权的[21]。
列斐伏尔常常把城市和城市化作为自己分析的基石,认为人造环境是对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22]。在国家处在空间生产核心的城市化过程中,设计者一方面用交通、信息和空间分割等技术手段卓有成效地强化这一过程,同时又促生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置身于资本主义主导空间中的设计师,其设计和规划无非是对空间进行抽象、归类和排列,以便为特定的阶级效劳。因此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与人和动植物毫不相干的抽象的中性空间,即可以承纳任何事物的容器。在列斐伏尔看来,奥斯曼的巴黎改建和尼迈耶的巴西利亚新城都是设计师分离和抽象空间的典型案例,在其中,是国家的政治权利主导了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设计只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
据此,列斐伏尔展开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规划精确的和分析的批判。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的规划,作为一种空间生产历史的特殊形式,它不是一个所谓关于调整分类并使之秩序化的一种实践,而是一种通过国家提出策略和按期执行的权力实践,它与按照指令进行消费的社会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其目标是从日常生活的每个可能的方面提取利益。[23]在这种实践中,规划促使了一种实际的分离——使身体的行为分裂,使感官迷失方向,并赋予视觉主宰其他的感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对日常生活进行社会的和有意义的规划,或者说这种规划在日常生活的节点中不存在,也不是说这种规划不能再运用。列斐伏尔认为,过去所有的伟大城市都是经过规划的,并且是非常有秩序的,但这些规划源于不同的本体论,这种起源生发于向死而生的不可避免性和悲剧性、嬉戏玩耍的生命性、宗教的神圣和性爱等,其规划的所有层面都由集体所从事和维系。而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具体的人已被抽空,死亡也不再对生命有意义,由此而形成的各种庆典不是遭到批判就是徒有形式,游戏(play)被无所事事(leisure)所代替,宗教的神圣性被商品拜物教所掩盖,性爱变成了仅仅是生殖性的。在城市区域中,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必然要贬低神圣性,从而顺利地推行其“理性”的规划。
因此,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规划不可避免地要对功能进行等级化和分裂,对空间进行同质化和抽象化,使日常生活极端的商品化和惯例化,最终对其规划的商品进行消费。这种对抽象空间生产的规划是在全球尺度上展开的,而需求、功能、场所和社会目标被置于一个中立的、客观的空间中。在表面上规划所做的工作是企图对城市的不规则扩展进行控制,并为居民生产出各种空间,但其结果是这些居民在对通勤、工作和睡眠的追求中趋向了一种毫无差异的一致的生活。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而出现的现代城市规划,通过控制、管理时间和空间的爆炸,进而控制和管理具有高度差异性的日常生活。[24]
尽管如此,在列斐伏尔批判资本主义的规划和其意识形态的符码时,并没有拒斥为都市生活做出一套规定和安排的必要性。他所要分清的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在其利益或交换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规划是如何将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分离,从而找到重新恢复日常生活差异性和统一性的可能。
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社会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由于空间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特征,因此,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日常生活的逻辑。社会空间不再是被动的地理环境,不是空洞的几何环境或同质的、完全客观的空间,而是一种具有工具性的、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种类的商品生产。空间成为消费行为的发源地,是大众媒介和国家权力等社会关系的生成物。对空间生产的规划和控制,就等于控制了生产的群体,并进而控制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更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割裂,并以匀质性面貌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同时消费主义也开启了“全球性空间”生产的可能性,而对差异性的普遍性压制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
五、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
在列斐伏尔看来,整个20世纪的世界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列斐伏尔批判了将空间仅仅看作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的传统社会政治理论,指出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三个特殊层面:
第一,列斐伏尔将空间看作是社会行为的发源地,空间既是一种先决条件,又是媒介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成物。列斐伏尔的“生产”概念,有别于经济学中被简约为工业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的生产表现为它对相关行为强加上某种时空秩序,具有束缚主体自由的功能。
第二,社会空间是资本与区域国家所产生的都市化建设环境与组织-机构基础下的“第二自然”,资本和区域国家的空间实践残酷地将使用价值得以实现的日常生活领域同一化并试图摧毁之,而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空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相互交织。
第三,社会空间是空间等级或规模(全球范围、国家范围、都市范围)的支架,在其之上,资本主义持续不断地进行区域化、非区域化以及重新区域化的过程。总之,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空间实践目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框架,对当地资本主义的充分理解只有将其摆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不过,尽管全球化趋势在日益强化,但是社会关系的很多重要方面依然具有区域性,“次全球空间”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
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理论划分了三个层面空间:全球化空间、都市化空间与国家化空间。资本主义的开启与压制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才能够实现,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促成了空间的生产,并形成了一个转化了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它产生了大量无法解决的矛盾,并最终导向资本逻辑以外的另类形式的空间实践,例如在当代工业化国家中,工人既不愿意选择为无休止的成长与积累拼命,又不热衷于通过暴力消灭国家,而是希望工作本身消亡。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它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所谓都市革命实际上包含着差异之间的生产、空间之间的吸纳与兼容、以及对自由时间的争取。最重要的是,只有在都市的背景下,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反空间”才能够被生存、被捍卫,并最终得以发展。正是从这里,即从这种所谓的城市的“空间缝隙”中,列斐伏尔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的出现。
城市不仅代表着地域与全球之间的中介,而且不断成为政治斗争和社会转化的场所。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包含少数民族、妇女以及其他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共同的联盟基础上,这些政治斗争对现有的权力压制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为它们不再具有人为设定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并且蕴涵着生成异质空间的潜在性[25]。
六、从城市理论到城市实践
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列斐伏尔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城市条件对于革命运动的制约和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使他更进一步意识到空间的生产。他将城市看作是充满生机、自由的日常生活的巨大的希望,并从1968年到1974年,出版了7部关于城市化和空间生产问题的著作。
城市是资本主义矛盾最激烈的场所,一方面,它揭示了理性化和同一化过程的无情专制,政府的城市规划就是这种专制的最清楚的显现;另一方面,城市凸现出由私人资产所造成的巨大的碎裂和分化。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本身是无力解决这种本质矛盾的,这也是使城市生活重新焕发活力的契机。他在“城市的权力”(The Right to the City)[26]一文中的宣言(正好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前)也就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行动纲领。
在该文中,列斐伏尔谴责了最近法国新城和周边地区的发展缺乏社区感和认同性,呼吁改变大型的城市、中心区、街道生活和居住区的构成,倡导有更多的自发性的机会。他相信,将城市看作是群众集体创造的作品,看作是人类正在进行的多样但又统一的创造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他对象征性的纪念碑和公共空间极为欣赏,但谴责虚假的如画(picturesqueness)和怀旧风格。受康斯坦特的启发,他提出一种多功能(multifunctional)和超功能(transfunctional)的空间和建筑计划,它将产生新的城市接触和交往形式。
由于列斐伏尔始终提倡理论结合实践,因此他同时与建筑师和学生一起致力探讨一种新的城市化的可能性。作为巴黎第十大学城市社会学研究所的主任,列斐伏尔不仅领导了由法国政府资助的城市研究项目[27],同时还积极地与建筑师一起参与各种设计和竞赛。在1960-1970年,他在建筑专科学校(Ecole Specialed’Architecture)开设课程和讲座,其思想和言论成为学生拒斥“鲍扎”(Beaux Arts)传统的宣言。在1970年,他与建筑历史学家创办了《空间与社会》杂志,但由于他对教条主义不妥协以及对空想主义者的拒斥,不久便离开了这份杂志。在1960-1980年的20年中,列斐伏尔的活动和写作对法国的城市政策的制定、导致城市中心的复苏计划的制定、创造更为民主的新城市运动巨型综合体的改造、以及在类似Creteil这样的新城的集体性的空间的创造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列斐伏尔很少对这些结果感到满意,他认为这都是政府的开支和有限的想像之间不可避免的妥协。他仍然认为城市转化要具有更多的诗意和实验性。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概念对法国最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的是1968年的红五月事件。他在南特大学给上千名学生开设的社会学讲座,给予了年轻的一代巨大的行动力量。更重要的是,列斐伏尔长期对日常生活系统化的批判以及社会转化的设想,给予了学运中各种离经叛道的组织以形成自己宣言的思想框架。列斐伏尔对体验、作为节庆式的日常生活以及在所有存在领域解放的关注,都是快乐时光出现的根本,这似乎短暂地实现了其对集体性、社区性、自发性和游戏的设想。
尽管“五月风暴”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对变革的诉求也很快就被新的系统和官僚政治所吸收,但是1968年标志着法国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并且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冲突和潜在性。在有些方面,1968年显现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概念的力量,同时也显现出了其局限性。从积极的方面说,“五月风暴”显示了日常生活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对例如广告、摇滚音乐、标语口号和媒体参与的必要性,显示了打破阶级界限、功能划分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划分,而形成一种欢乐和交往的新的形式的可能性。从消极的方面说,“五月风暴”揭示了一种开放的抵抗系统化模式的困难。
事件的参与者竭力推行变革并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例如使巴黎美术学院非中心化,许多系和专业分散到其他的院校中。尽管快感非常短暂,然而个人和社会解放的设想进入了大众意识,它对社会风尚、女性实践、家庭生活、阶级冲突、性别和种族问题的改变以及在随后的十年中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都做出了贡献。在文化范围内,“五月风暴”就像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概念一样,模糊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前卫的侵进和大众的愉悦之间的界限。
七、结语
对列斐伏尔的阅读,有必要沿着其思想的空间化历程,进入与列斐伏尔的真正对话中,这种对话可以看作是自我反思的一种空间化的尝试,而反思是列斐伏尔在其思想和实践中贯彻始终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达致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但这种对话和反思却能够保证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特别在城市层面上)是如何展开的进行正确评价和理解奠定了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列斐伏尔思想的丰富性、知识的严密性和历史的纵深感。
当然,有学者,如美国城市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批评列斐伏尔的空间和城市理论是一种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分析理论,对城市社会的许多决定性因素的认识过于抽象化,从而阻碍了城市空间研究的科学突破。但笔者认为,列斐伏尔并不是要抛弃科学式的研究,而是要使空间研究具有现象学的纬度,并重新立于存在论基础之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尔对列斐伏尔的批判就显得有点偏颇和不得要领了。
注释:
[1] 尽管有学者认为由于曼纽尔·卡斯特尔(Castells)对列斐伏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列斐伏尔进入英语世界,但更为客观的原因是其主要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才被译成英文。
[2] 爱德华·W.索加,《后现代地理学》P73,商务印书馆,2004,北京
[3] 这一思想同样也受到了天主教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构成列斐伏尔乌托邦思想的基础。
[4]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认同萨特的思想,列斐伏尔还是对处于鼎盛时期的萨特和存在主义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嘲笑萨特等哲学家,认为不如将他们对本体论或宇宙论的论述留给诗人和音乐家。
[5]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P010,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 关于日常生活与建筑的问题可参见2004第8期《建筑学报》中 “日常生活批评与当代建筑学”一文。
(7] 从列斐伏尔1947年出版《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至1972年“日常和日常性”发表,其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发展了近30年,也可看出这一思想在列斐伏尔的思想中贯彻始终。
[8]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P.14. Tr.Sacha Rabinovitch, Lodon, 1971
[9] 汪原,“日常生活批评与当代建筑学”,《建筑学报》2004.8,
[10]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因而他特别强调前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不同,并通过强调这二者的差异来揭示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根本特点。
[11] 尽管德·塞图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但德·塞图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单一性和专制,强调掌控情境和创造自治的活动领域,将其称之为对抗规训的系统的个体能力。
[12] 列斐伏尔并没有认识到乡村节日同样可以被系统化,而米兰·昆德拉在《玩笑》中对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乡村庆典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1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P181
[14]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P26
[15] 参见《新建筑》2002/1,“《空间的生产》和空间认识范式转换”一文。
[16] 同上
[17] 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带有较强的海德格尔色彩,而且深受其早期的日常性(everydayness)概念的影响,但他同时又批评海德格尔关于意识的纯粹现象学观点和悲观主义,批判海氏对人的思考脱离了历史和城市。
[18]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P7
[19]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P106,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0]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P117
[2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P282
[22]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P227
[23] Jonathan Hughes & Simon Sadler,Non-Plan, P86
[24] Jonathan Hughes & Simon Sadler,Non-Plan, P87
[25]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P166
[26]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P147
[27]在1960-1970年,法国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如福柯、德鲁兹等都承担了由政府资助的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在这段时间中,城市社会学比其他的社会科学获得了更多的资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社会学法国学派的发展。 |
|
纯粹建筑 | 理想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