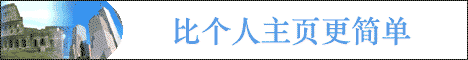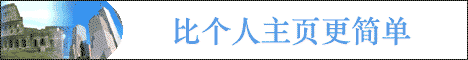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 本文发布于
2013-07-03 11:24:17
□ 现有评论:0
□ 查看/发表评论 |
|
|
不透明的世界的透明性
|
专栏
唐克扬
不透明的世界的透明性
什么是“透明”?很小的时候,大约是七十年代末期,尽管我的城市里还有连片的土房,玻璃已经不是个稀罕事了,但是大多数都还是那种劣质的薄片玻璃,时有杂光,掺带杂色,“晶莹透明”是谈不太上的。因为玻璃难得更换,大多数时候,也就沾满了尘,雾霭和各种成分的油腻。现在想起来,这种无法防止也难以清除的“脏”,其实,是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某种“中国性”的一部分。
在需要的时候,这种不甚透明的“透明性”是可以摆布利用的,比如厕所、浴室和其它不欲人们窥见的室内空间的开口,就需要覆盖这种暧昧的不透明玻璃,稍加装饰图案,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钻石玻璃”这样的“廉价出奇效”的装饰材料。倒过头去看八十年代的不显山显水的“透明性”,那时我们似乎是用一种低成本的设计,达到了今天用高档夹胶玻璃,电控调光玻璃才能达到的质朴效果,有时候这种效果甚至比今天的“过度透明”会更好,因为至少对于那些年月陈久的住区而言,只有这种“不透明”才有着和我们欲语还休的生活相匹配的丰富层次。
无论如何,玻璃在中国的历史并不能算很久。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始建的北京南堂(圣母无原罪堂)已经大量使用所谓“明瓦”,而大约同一历史时期,初次尝新的雍正皇帝在养心殿卧室所安的所有玻璃,却抵不上一所教堂所有玻璃的一个零头,足见还是昂贵的物事。据说,这是因为威尼斯的玻璃工匠妥善地保存着他们的秘密,不欲外人知晓——但这也许终究只是个传说罢了。事实上,东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皿早已传入中国,只是中国人对于“透明”这种属性一直都不那么熟悉,李白写道:“却下水精(晶)帘,玲珑望秋月”——多么优美的画面!但中国人似乎分不清属于液态的玻璃和固体的水晶(水精)的区别。是当代建筑理论家比如柯林·罗(Collin Rowe)这样理论家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西方人说的“透明性”(transparency)并不是等于真正意义上的“全透明”,其原因很可能是相对于他们早已有之的全透明(光线损耗为零的情形),透明性这个词实际上说的是一种程度,而对于一向“善于包藏”中国视觉文化而言,看到了和看见了似乎没有区别——我们要么是不透明的,要么又是赤裸裸的。
我第一次感受到“透明”原来是有层次的,是到了美国之后。我“天真的眼睛”一下子感受到了巨大的不同,在那里的民用住宅大多使用真正透明无色的超白玻璃,就连城市中第一层的房屋也经常使用巨大的落地窗,并无防盗栅栏,并且入夜之后不一定拉下钢铁卷帘(当然,在各种骚乱的晚上,这也就造成了形形色色的“水晶之夜”)。现代主义的钢铁框架摩天楼的观感无法脱离这种奇观式的透明性,和前现代社会包藏着的室内迥相其趣,在芝加哥,我曾经居住过贝聿铭早年设计的55街大学公园公寓(University Park Condominium),直观地,经年累月地感受了这种透明性,在那里玻璃一直接到竖向结构和水平楼板,造成立面上不加掩饰的巨大孔洞,向南的窗户极大,几乎把没有人工通风的方盒子室内变成了一个温室。
我喜欢现在我家纽约的住处也是因为它的几扇宽大敞亮的窗户。更有甚者,起居室朝向室外的是整面的落地窗,对着一个不曾包上的露台,落地窗虽然是双层的,但玻璃很干净,某种意义上,就让这间客厅直接暴露向了远山。有段时间的白天,我长久地守在这里,一边倚在沙发上看书,一边近距离感受着窗外全方位的晨昏变换,一切真真是透明的,和我之间仅仅有一层薄薄的玻璃。这个时候,你就格外真切地感受到透明度的变换,尤其是凛冽凉薄的冬日,随着屋里温度的增高,水汽慢慢在窗玻璃上堆积,渐渐增加出更多的层次;看着看着,天色向晚,屋外暗下来,屋里的灯光染遍屋里的每一个角度,但是却无法侵入屋外广大的黑暗,倒是把我的影子映在玻璃上了。就在这个时候,偶然在靠窗的茶几上点亮一盏烛台,我发现在玻璃上的光影不是一个而是数个,当你坐得离落地窗更近,就会发现即使是玻璃片也是有厚度的,这种浅浅的深度尽管很难辨别,它却是此刻的晦明交际处混沌的氛围的来源,并且通过人脑和反射的放大留下深深的印象。当你仔细打量这些时,你就会慢慢忘记了真实的世界,进入一个向着不可深度潜行而去的长廊之中。
我一直着迷这种现象。有没有可能在室内设计之中更明确地表达—揭露这种现象?隐隐约约地,我体会到它不一定是玻璃和原设计本身的预设特性,而是前面提到的,某种“现象的雾霭”的产物。这种““现象的雾霭”事实上改变了空间“全透明”的属性,但是反而比那种“恍如无物”的清洁的现代主义更生动了。
位于798的某画廊建筑是是特殊时代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透明幕墙的构造和画廊的功能生来就是拧着的,首先是造了一个完全不适合做画廊展示用的玻璃幕墙加上简易屋面的盒子,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就是房主锲而不舍地持续改造这间“非画廊”,直到把它改动得面目全非,他用石膏板墙糊上了原来的玻璃盒子,除了西南角突出的一角,现在这个盒子又四面不透了,变成了一种内外逻辑完全脱离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它无法一下脱胎换骨,而只能消化前面的状况,每一个局部逻辑链条基本完整的情况下,整个设计却是支离破碎,理性的“明镜台”上真实是尘埃满面的状况。
换一个角度思考,也许这种蒙昧便也是中国式样的“透明性”另一个层面上的来源。与其改头换面逆流而上,能否顺天应命?我们也许可以不追求字面意义上的透明,而发现从一种混杂的困境中抽身而出,“忽然有光”的“奇迹”——能不能不只是“解决问题”,也从问题的解决中生发出建筑的意义?
我的改造设计面对的主要问题有三样:其一是要有个合用切题的室内——就现行美术馆的基本功能而言有些东西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比如一侧的直射光对于展品的干扰;其次还要设计出一个起码的展程,使得出入和观瞻有着更好的联系,包括对于室外广场的改造;最后,是如何在创造新意的前提下,尽量利用既有的条件,不至于完全推倒重来,尽量有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意思。在中国的国情下,第三点也许更加有意义。
结果是利用石膏挂金属网结构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半透表皮,它带来了听似奇特的“(随光强)有深度的透明”,“(随地点)不均匀的透明”和“(随时间)变化的透明”。对于建筑室内的整体改造,我感兴趣的一个最主要话题是:如何可以让厚重同时有光?如何自成一体的同时向外界开放,如何在喧嚣里听见安静?在视觉语言上,我的设计并不追求第一印象的“动人”,它致力于对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边缘特质的探索。
这样又“透”又“不透”的白墙可以保证基本的展出环境,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还可以让室内和室外有良好的互动。在晚上看上去它就是一面普通的白墙。但是一旦下午的阳光投射上去,人们就不难发现这堵白墙的不寻常之处。它所承载的透明性不是普通的穿孔板和网眼板可以做到的。因为这种透明性是逐渐“渗透”进去的。
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与这种透明性联系在一起的普遍问题。其实,除了手工和物理的构造之外,一定还有别的办法达到这种既透明又不透明的“奇迹”。西方人早已先行一步,透明混凝土是在普通混凝土浆料中掺入一定比例的玻璃纤维使得它既坚固又透明。我则想到,是否用其它轻薄透光的材料比如纸浆掺和在混凝土中也能有这样的奇效? 我们既无法承担实验费用,也没有什么厂家愿做这样的实验,但基本思路似乎是清楚的,巨型建筑用在立面上调配开窗大小比例的方法来控制一座建筑的“透明度”,微观上的“透明性”也是把一定数量的“透明”掺入“不透明”,只不过在人的尺度上,在室内设计项目中的感受元素更微细,对于需要不动声色的节点的设计的要求也更高。
后来有机会迎来了第二次“透明性”的改造:这一次室内的“内容”如今也成了室内的一部分,因为我是这个艺术展览的策展人。碰巧,展览的主题正是关于“透明”,这一次的“透明”是通过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反转”——达到的,既直观又抽象而且一定程度上“非建筑”。“反转”本是摄影中一种并不少见的技术,感光胶片上的世界原本就该是“反转”的,看上去难以真实,冲印照片,再次“反转”,就会将中间状态的负像恢复成人眼习惯的“正片”,负负得正。黑白正片的感色性仅限于紫蓝色光,黑白“反转”的结果因此不像彩色正片,实际应用也较少,可是,有一位艺术家把高反差的黑白正像再次变为负像,它改变的不是色彩关系成为明显的不存在的事物,而是成了一种微妙的反转的现实和另一种“透明性”的来源。
这位艺术家拍摄的对象残佛来自云冈石窟。在南北朝时代,“反书”是一种新兴起的视觉现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家、画家和书法家都试图同时看到世界的两面”(巫鸿,《中国早期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于是,在梁文帝建陵前的神道上我们看到了一对互为镜像的铭文——“太祖文皇帝”的“正”“反”两种写法——它既是对称也是“颠倒”。
视觉表现本是互文的,无所谓黑白正反,因为视觉表现中的实证性(positive)命题(方的还是圆的)常属绝对,规范性(normative)的感受(黑色还是白色)却多少依赖于相对性的错觉——“形状是绝对的,所以在你画任何线条的时候都可以说它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色彩却是全然相对的”(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但人的身体是左右对称而分前后的,这带来了文字书写天然“正反”的区别,通过区别此界和彼岸,一个身处生和死,凡俗和天国边界的观看者得到了非常强烈的空间深度的信息。由平面到立体,这种反转带来的差别就好似反转片之区别于寻常照片,它使得观者“看进去了”。
就其空间意义而言,云冈石窟呈现出较强的“西方”影响向中土范型嬗变的转折意义,此处也是中国寺庙向“前殿后塔”格局过渡的关掖点。依据北魏时期的记载,那时的佛窟依然保留着印度石窟寺的类似用途,流行于云冈的中心塔柱,表明早期佛寺依然保留着以塔为中心的格局;但是,大多数佛窟又残留着原来窟檐(门-面)的痕迹,或是自身干脆成为一种拟似的石质建筑空间,这便给洞窟中的法体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是中心对称因而接近佛教的转轮时空,还是左右呼应而有“前”“后”?
“颜上足下各有黑石, 冥同帝体上下黑子”(《魏书·释老志》 )——著名的“昙耀五窟”中有平城时期诸帝真身的传说,至少是显示了这么一种可能:佛教空间的礼仪模型,已经和世俗崇拜的需要并行不悖了。它们其实不一定会自相矛盾,相反倒可能相得益彰,这是巫鸿先生所说的另一种“阈界位置”,也就是产生双重意义的二元图像的位置。如果说恢宏的窟门是毫无疑义的“进入”,洞中陈列千佛的佛龛却有待模糊的感受,它们既可以是盛满形象的均一“宇宙”,也可以是突出帝-佛世尊的特出“座位”,前者可以在冥想里渐趋混沌,后者却因强烈的等级而有确定无疑的方位。
摄影家的作品正是这种二元图像的再创作——当他把残缺洞窟的画面“反转”以后,意想不到的情况不是佛像的“消失”,而是在于它的“重现”。三维的洞窟投影为黑白照片后,强烈的进深消失了,只剩下凹凸图底的关系,当明暗转置之后,大面积的暗色取代了明亮区域,如果还循着原先空间进深所设定的观览定式,原有图像的前后便发生了逆转——现在,仿佛是佛在后,墙在前——如果图像本完好无缺,那么,在清晰的空间再现里,底片般的它看上去就是一个悖谬的画面;可是,佛像的轮廓还在,而且因它的不完整而给空间阐释留下余地,由于格式塔般的心理机制,一个幻觉性的整像便沿着残损的格局,在观者的感受中油然浮现,在画面的“前”“后”来回扯动。
原本坚实的墙面消失了,它也因此变得“透明”。
我新的“透明性”设计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除此一点之外,这个设计只是一个常规的设计。奥妙在于一种物性两边不均等的介质,一种有意而为的“反转”和“翻转”:一边坚固,一边透明,但是两边的物象则同一。“正像”提示着由一个不可穿越的“正面”,反面的“负像”却是一个没有深度的趋于消失的幻境。
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艺术与错觉》里面,贡布里希早就说过:“所有的艺术发现都不是对于相似性的发现,而是对于等效性的发现。这种等效性使我们能按照一个物象去看现实,而且能按照现实去看一个物象。”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空间都不是在字面意义去构造某种感知,而是找到一个与经验同构的途径。这种途径使我们能按照我们青睐的感性去分析建筑构造方式,而且能按照特定的建筑构造方式去还原某种感受



 |
|
现有评论:0 [查看/发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