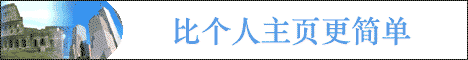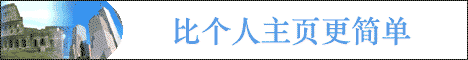|
|
|
集体公共空间
abbs
|
贾斯廷-麦圭克
城市“集体公共空间”(commons)和服务增加,有希望在单一的城市开发政策之外,为更好地开发城市,提供一种公众分享的选择。但这种努力如何从当地公园项目的水平更上一层楼,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集体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一种选择
目前,谈论“城市集体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原因很清楚。传统上所谓的“公共概念”在退缩:政府公共服务处于紧缩政策的摆布下,政府公共经济住房被出售,政府公共空间越来越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在一种不屈不挠的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中,“集体公共空间”似乎对政府和私人之间的较量提供了一种选择。公共拥有和使用土地或服务的概念的谈论,是一种21世纪的敏感词。用行话来说,就是“公民参与”和“对等生产”等。至少,从理论上讲,“集体公共空间”完全有基本的潜力。
然而,为什么在任何时候,城市“集体公共空间”被提及时,都涉及到社区花园?而新的城市政治的创始者总是种植甘蓝和大黄(食用大黄)。
“集体公共空间”按比例地增加,能影响一个大都会的运作方式?能够处理诸如住房、能源使用、食品分配和净化空气等问题?换句话说,城市能被作为“集体公共空间”来设想吗?或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扩大“集体公共空间”吗?
英国有独特的,不断地写进伦敦的档案的“集体公共空间”的历史。温布尔登(Wimbledon)、克拉彭(Clapham,)、伊林(Ealing),都有集体公共用地。在些地方,英国人的祖先曾经有权放牧他们的牲畜。
但十八世纪的“圈地运动”将大部分的土地转入私人手中,把它变成一种可销售的资源,创造一个无土地的工人阶级。
在今天,“集体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是,人们仍然倾向于把它当作一种公共资源,不管它是海洋、河流还是鱼类资源。
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人们不能在没有一个共同的管理战略的情况下,拥有共同的资源。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认为,“集体公共空间”需要一套法规。
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获奖理由是,她证明,如果有一个起作用的制衡系统,这些公共资源不会屈服于所谓的“集体公共空间的悲剧”(某些人会取得比他们应分享的更多的资源)。
“集体公共空间”最好理解为一个动词
因此,与其说“集体公共空间”是一种资源,倒不如说是一种程序,一种由人民的团体分担责任的社会关系的架构。比如,分担一个花园,甚至分担他们的街区的管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莱恩博(Peter Linebaugh)说的,“集体公共空间”最好理解为一个动词。
目前,“集体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念流行,部分是受互联网的推动。还有一个推动力是,网络工具使大型群体从事这方面的组织和宣传更加容易。
开放的代码软件,维基百科网站(Wikipedia),这种有创意的“集体公共空间”和社会媒体,使知识共享成为可能,同时证实了这种水平组织的气质。
在城市,获取“集体公共空间”,更经常采取在剩余的土地上,或在一些楼房间隙建设花园的形式是很明显的。因为土地有限,并且,因为建设花园比建设楼房更容易获得批准。
但甚至建造花园的创新行动也经常受到威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 试图卖掉100多个社区花园。在柏林,最近发生了为了保护废弃的滕伯尔霍夫机场(Tempelhof)的绿地,民众与开发商的斗争。
事实上,这经常是“集体公共空间”主张自身权利的理念的紧要关头。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在伊斯坦布尔的盖齐公园(Gezi Park),在纽约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通过民众的抗议运动接管了这些地方(祖科蒂公园除处),将国有的空间,改变为临时的“集体公共空间”。
类似的情况是,希腊的经济危机,在雅典导致“集体公共空间”的复活。被市政当局忽视的公园,开始由居民团体维护。在巴西的贫民窟,有大量的“集体公共空间”出现的例子。在那儿,许多社区以共建“集体公共空间”和共同管理环境为骄傲。
通过共属住宅创建幸福社区
问题是,是否“集体公共空间”以它强有力的政治维度,一方面能超越极端的需要和象征性的抵抗;在另一方面,“集体公共空间”是否是无害的本地创新,并且有令人鼓舞的例子。
正在开始以很大的规模和复杂性完成的“集体公共空间”项目,出现在巴黎郊区的科隆布。从2012年以来,Atelier d’Architecture Autogeree建筑事务所开发的战略是,它的共同主任多尼亚-佩特雷斯科(Doina Petrescou)说的“自下而上弹性恢复战略”(bottom-up strategy of resilient regeneration)。它超越了典型的城市农业创新。
真实的情况是,科隆布的“集体公共空间”,有一个集体使用的微型农场,但只是三个项目之一。另外两个项目,是微型再循环利用工厂和共用生态住房。
按照这个创新计划,现在有400个市民共同管理5000平方米的土地,生产食品、能源和和住房,同时积极约束废物和用水。
按照欧洲标准,这个创新计划是一个可选择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大规模的试验。但更大的目标是在今后5年内,增加5个以上的这种综合项目,并且将其发展为一个以“集体公共空间”为基础的市民运动。
这只是个案研究,证明数百名普通市民,而不是活动分子,可以创造一种非传统的城市经济。
然而,总是出现的问题是,“集体公共空间”包括了哪些人?与为所有人的利益的,由政府掌握的“政府公共空间”相比,“集体公共空间”可能更容易成为“飞地”(enclaves)。
在“集体公共空间”的人们,往往是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数有限的、利益相关的群体。当外来者主张对所谓的“集体公共空间”的权利时,会发生什么呢?
希腊“空间政治”(spatial politics)学者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德斯(Stavros Stavrides)指出,“集体公共空间”仍然是一个开放的社区,它必须能吸收新来的人。
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德斯最近在伦敦的一个关于“集体公共空间”的演讲会上说,“集体公共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不断地吸收那些能够参加的人。
“集体公共空间”要求“体制创新”
社区变得越大,社会关系就越复杂。但这不会必然是一个障碍。更大的挑战似乎是,“集体公共空间”能否在不给社区以过度的负担的情况下维持下去。
近年来,最鼓舞人心的创新社区之一,是马德里的Campo de Cebada社区。这里原来是一块废弃了的土地,一些建筑师和本地的居民,将它改造成一个公共广场和文化空间。
但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朱罗亚克(Zuloark)最近承认,他们都厌倦了。因此,“集体公共空间”需要有“可持续性”。否则,它的理想主义的潜力,就会与它的成功的必要条件的不实际低估发生冲突。
英国最近的政治话语没有新意,甚至冷嘲热讽,是错误的。保守党的流产的“大社会”(Big Society)议程,乞灵于一种模糊的志愿服务体制,弥补地方政府的预算削减。
英国的雇员的工作时间,是欧洲最长的,他们却被期望为他们的社区服务?由于“集体公共空间”思维方式兴起,他们需要超越“礼物经济”(gift economy)的概念,并且进行系统重组。
希腊“空间政治”(spatial politics)学者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德斯指出,由于“集体公共空间”的概念和实践成为主流,要求有新的管理体制——特别是新的政治体制。
到目前为止,“集体公共空间”的政治的灵感来自欧洲以外的国家:来自玻利维亚的科恰班巴市(Cochabamba)的水上“集体公共空间”系统,或者来自墨西哥恰帕斯市的Zapatistas“集体公共空间”,或来自最近在科巴尼(Kobane )的叙利亚库尔德人。
但这种情况可能在改变。随着西班牙“巴塞罗那集体公共空间运动”(Barcelona in Common)的成员艾达-科劳(Ada Colau)最近当选市长,“集体公共空间”的管理体制终于在一个重要的欧洲城市有了立足点。
如果“集体公共空间运动”像“巴塞罗那集体公共空间运动”那样参与政治决策,那么,“集体公共空间”可能开始重塑人们对公民权和可持续性的理解,并且使有关话题超越建设花园。
本文作者贾斯廷-麦圭克(Justin McGuirk)系英国《卫报》建筑评论家
图片说明:

1、巴黎郊区的“田野城市”(Agrocité)项目

2、最早的城市“集体公共空间”之一——伦敦南部克拉彭“集体公共空间”。

3、2013年6月,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民众抗议拆毁盖齐公园(Gezi Park)。

4、巴黎郊区的“田野城市”(Agrocité)项目,包括微型农场、废物再利用工厂和共同生态住房。

5、马德里的Campo de Cebada社区
·发表评论 |
|
[更多评论]
[更多推荐]
|
|